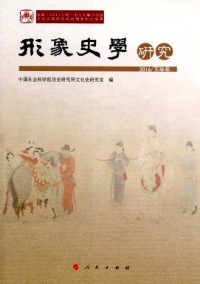祭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祭父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祭父范文第1篇
祭父范文第2篇
作為嚴歌苓小說《金陵十三釵》的電視劇版,《四十九日?祭》以審判的形式講述南京被日軍攻占前及日軍進城之后49天內發生的人間慘劇,反映絕境中的生命意義與人性救贖。
拍攝題材是導演張黎的心結,他為此籌備多年。張黎說,這個片子不僅希望中國人看,更希望發行到全世界。
找一個主題也要拍
日軍屠城六周,《四十九日?祭》的故事從事發前一周寫起,加起來一共49天,49天也正好是中國傳統中,人去世后靈魂得以超度的節點,這是劇名的由來。
早在1991年,張黎和編劇嚴歌苓就開始聊作品,探討歷史的本質。2011年底,拿到小說《金陵十三釵》后,張黎、嚴歌苓及這部劇的總策劃張和平,投資方負責人等開始商量,一定要找一個主題把它拍成電視劇。 ”
張黎表示,拍《四十九日?祭》有兩個意義,一是審視,二是警醒,《四十九日?祭》是一個有關浩劫的故事,一個記錄屠戮的故事,一個從來沒有被遺忘,也絕不該被遺忘的故事,希望世界可以知曉,國人以此牢記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城市曾經發生的一切。“在這部劇里,生命是平等的,更是有尊嚴的,我們用絕境求生揭示生命的意義:與其屈辱活著不如尊嚴死去。”
擅長宏大歷史敘事的張黎曾執導《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人間正道是滄桑》等歷史大劇,張黎的作品有種難得穩定的厚重感,又不乏引人入勝的戲劇沖突和情感表達。張黎一直認為,一部歷史劇很難還原遙遠年代人物的真實樣貌,有的只是再塑造的過程,塑造的尺度不在于人物外貌的相似度,更在于精神的傳達。有很多史學記載,嚴歌苓通過幾個真實的人物把它戲劇化成一個故事,這種提煉在張黎看來就是一種精神真實。
“一個貌似凜冽的故事,背后都絕不是歷史本身,而是一種人文精神。我導演的片子本質上有一個相似的東西,就是居安思危的主題。”張黎表示,《四十九日?祭》中沒有設計表現日本人善良一面的戲份,因為個體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一個族群,一個千夫所指的族群。
小說《金陵十三釵》在西方出版后,很多人才知道中國歷史上發生過這么大一件事。嚴歌苓說是一次不同尋常的事件,一定要想辦法讓世人了解,“這就需要打破反日題材常規的思考習慣、創作習慣、審美習慣,讓別人在藝術上被感染了以后來認同和相信你。”
劇版更接近原著
關于《金陵十三釵》,已有張藝謀的電影版,電視劇版如何做出自己的特色?
首要的區別在于劇本容量。受篇幅所限,電影版必須舍棄很多對的思考,電視劇版中,嚴歌苓新增了大量素材和新鮮感受,將原著改為長篇,并把她多年來對的研究納入其中。
情節和角色設置上,電視劇增加了“前史”和“后史”,人物故事也會有一些改編。電視劇中同樣有神父,有宗教,有租界里各式各樣的外國人,但電影版中的外國神父在電視劇中變成了由張嘉譯飾演的“偽神父”――中國人法比。劇版要表現的主題之一是,“你是什么族群就是什么族群,永遠不要奢望別人來救你,外國的神無法救中國的人。”劇版中,女主角玉墨不會說英語,她沒有“凋零”而是作為戰后幸存者參與了大屠殺清算,女學生書娟也比電影版更陰郁。嚴歌苓表示,總體上,劇版更接近原著,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能在電視劇里更完整地展現,“身為作者和這部劇的編劇,這是我最愿意也最愉悅的一次作品呈現。”嚴歌苓說。
劇版不再是兩個女性群體的命運互換,而是更為關注大屠殺中的群像,“片子里可能沒有特別絕對的男一號女一號,多條線索相互勾連,它是群體命運而不是個體命運。”劇中,無助的學生、顧盼的風塵女、忠于國家忠于信仰的士兵和神父、屈服妥協的漢奸,他們在災難來臨時,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同樣的恐懼,在自救與救人中,他們之間締結了純真的愛情、友情和親情,曾懦弱的變成了勇士,曾迷失的找到了方向,曾虛無的得到了收獲,曾有罪的完成了救贖。
張黎說:“《四十九日?祭》概括來說,就是幾個男人為了身后各自的女人一個個去死的故事。我們希望打撈歷史,在大悲劇中挖掘生命本質,真實還原人性的選擇和情感力量。”
祭父范文第3篇
本書(《〈喪禮撮要〉箋釋》,以下原著簡稱《撮要》、點校本簡稱《箋釋》)據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曾祖彭天相先生《喪禮撮要》抄本點校、箋釋,本書為原著者國子監肄業后任民國長沙某工會主席期間著成《四禮撮要》[清代朝鮮學者尹羲培亦作《四禮撮要》,筆者見有朝鮮哲宗元年(1850年)木活字刊本]之喪禮部分,不免有脫漏、訛誤、謬引之處。故此次點校,因抄本之序、跋亡佚,無可稽考,故只錄鈔并覆合撮要自“初終”至“禫、吉祭”部分。既為撮“喪禮”之要,即以朱子《家禮》、司馬《書儀》、鄭氏《書儀》所錄之喪禮為底本,本次箋釋所用之史料,分五部分:一是以漢魏古注、唐宋注、清注《禮記》《儀禮》之喪禮論述作為原始參考。二是參照《開元禮》《通典》《五禮政和新儀》《大明會典》《大清會典》等政書類之喪禮部分(如國史之喪禮、兇禮部分或《五服圖解》《吾學錄》等宋元以來官方禮典)作對比參考。三是未收入上述典籍、但喪禮有專書論述,如《士人家儀考》《讀禮偶見》等。四是明、清域外學者之喪禮著作,如朝鮮學者《四禮便覽》《疑禮類輯》《喪禮備要》《常體便覽》等。五是各姓部分族譜所附錄喪葬禮部分。
凡《撮要》有引他說而未注引出者,如“賑災全儀”之《圣旨》部分,引自《大明會典》之《厲祭》與《告城隍文》,箋釋時注明所引古籍,且衍文一并稽核補足。
凡《撮要》所涉及之喪禮條,他說有更為詳述者,一并箋釋于此條之下,如品官銘旌長度,本書僅見錄清代“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下七尺,士庶人五尺”,箋釋部分一并補足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歷代品官銘旌尺度。凡《撮要》涉及之喪禮專有詞匯,箋釋時先釋后箋,即先解釋詞語,后因他著中有涉及此詞匯之句,以資參照。如:
釋「棄捐。捐即棄也。說文曰:棄,捐也。捐,棄也。人死之婉辭也。
司馬太史公曰:有先生扁鵲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李翱之楊公墓志載,公〈素〉生六年,太保棄捐;未及成童,虢國又終。宋濂之故封承事郎給事中王府君墓版文:予生發未燥,先公棄捐,一念及茲,肝膽為之拆裂。錢謙益之尚寶司少卿袁可立前母陸氏加贈宜人,新昏燕爾,中道棄捐。哀哉若人!趙翼之哭劉瀛坡總戎,如此相知忍棄捐,身騎箕尾竟登仙。
《撮要》收錄之祭文、祝文、告文較為精短,他著有收錄類似文體者,箋釋部分也一并收錄。圖表引自古籍者不再標注,但列文獻于文尾。
筆者的高、曾兩代,均是國子監生與奉政大夫,但作為知識精英的地方紳士(Scholar-Official),他們并沒有在“國朝治化”中展現出積極的姿態,僅僅是五品閑差的曾祖,終其一生也不過在他二十余歲時以不足三月的時間就任一蕞爾小官——長沙某工會主席。或如清人金榜在《禮箋》序言中所說,“學問之道,寧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作為深諳明堂祫禘之道的曾祖,自然知悉祭祀之本意乃在“于心有安”,或許,學問之本意也該在此。光緒十九年(1893年),高祖在未完成彭氏續修族譜修撰便從然卒去。民國十年(1921年),湘鄉彭氏諸縉紳公議修撰彭氏三修族譜,諸公推曾祖為三修總撰,同為奉政大夫的京官彭維廷在族譜序中盛贊曾祖為“老師宿儒”,時年曾祖不過二十多歲,恰是筆者現在這個年紀。
筆者已經記不清是在何時進入對家禮的研究,就在一年前,《南通大學學報》刊發了筆者《中國古代的家奠弔祭制度》(2009年第1期,即本書摘要)、《社會科學論壇》不吝冗繁,為我《昭穆制的歷史意義與功能》長文連續四期刊載時,人們便開始追問同一個問題:是不謀而合,還是家學淵源。筆者只能引據歷史學家席文(Nathan Sivin)對家學或學派的定義來告知他們,這只是一個巧合,絕非家學:“某一大師特有的學說或技術的傳授過程,這些技術或學說,通過私人傳授由其信徒代代相傳,強調權威性經典在世代流傳過程中的完整性。”
首先,據筆者所知,熟讀禮經的曾祖在某些觀點上尚不如筆者了解透徹,故不可謂稱為大師,例如他斷定:
祠堂設置高、曾、祖、禰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
很顯然,他的這種見解有悖“左昭右穆”的本義,在《箋釋》中,筆者便引用了清代帝廟中的神主排列位次辦法來回應曾祖對四代神主位置的擺放:
皇清廟制,太祖高皇帝正中南向,孝慈高皇后配;太宗文皇帝東位西向,孝端文皇后、孝莊文皇后配;世祖章皇帝西位東向,孝惠章皇后、孝康章皇后配;圣祖仁皇帝東次西向,孝誠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配;世宗皇帝西次東向,孝敬憲皇后配。此言以左昭右穆,妣并配享。此處以高祖居西,則循古者西鄉為尊之意,著者以西至東定昭穆尊卑,似與昭穆本意相去甚遠。
不過我們通常說“禮以時為大”,此說亦無可無不可,只不過筆者認為學問之體認,總在以靈活變通為要,太過局瘠狹隘,則成不了氣候;又比如曾祖認為:“將祔新主,先期于祠堂祭告各龕,舊主祭畢,奉高祖神主安置他龕。”曾祖對“告遷”這一概念的理解無疑是準確的,但是在書中,他并沒有交代清楚清代告遷禮的根源與動機,在《箋釋》中,筆者便以《茗洲吳氏家典》經典詮釋做了補征:
明清以來之祠堂,神主不祧,日積月累,有入無祧則有數百神主,累世而百代之后后嗣不得辨其先祖。考茗洲吳翟所著《家典》曰:近來宗法不講,而吾族地隘力綿,又不能遍建宗祠,各以支派祔序一堂,由來舊矣。顧祔主日增,而祧法不行,雖則廟貌極其宏敞,勢必昭穆不明,長幼無序,名為禮盡,實為違制;名為仁厚,實為悖理。此乃明清之際祠堂之眾況。故亢宗大族者有迭毀神主及新主遷祔之制。即所謂不祧之祧,另立兩龕,萃有后曠祀之神主暫藏之,俟其子孫動報本之思,親潔粢盛,以致孝享,當仍敘死者之昭穆,一體遷祔。
其次,筆者的“家學”并非代代相傳,高、曾兩代人的學問在祖父一輩時已然殆亡。曾祖給祖父起名為“淑人”——《小雅》曰:“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又因祖父排行第三,按清代命婦之級別,“一品曰夫人、二品亦夫人,三品曰淑人”,曾祖對這個名字的選擇或許真是一字成讖,祖父在青年喪妻、老年喪女的窘境中度過了苦長的六十余年,反而練就了他嚴謹求實的“懿德”,但是他對學問的仰止無疑是虔誠的,且終其一生從未停止過,這種渴求也完全寄托在了我身上。在祖父雙眼失眠、暮靄沉沉,行將歸彼大荒之時,他尚在筆記中寫道:“籠中鳥、網中魚”“百余棄杖”,嗚呼!不自由毋寧死,豈非一代讀書人從一而終的追求?故而可以說,我今日之學問與品性,完全得益于祖父而非曾祖。
再者,從《箋釋》文稿不難看出,筆者與曾祖的諸多觀點相左,嚴格來說,該著的箋釋已經不具備席文所定義的“完整性”。曾祖認為禮學可以“撮要”,取折衷之言為便,這與清人王心敬的《四禮寧儉》(亦可參見朝鮮學者《四禮笏記》《四禮撮要》《喪禮取要》等書觀點)的行文是一個套路。但我始終認為,禮當“以人心為安”,然而如何使人心得安?則必須回歸經典,對于那些歷史失憶(Null of history)的問題反復考索,從經典的提示中找到自己的見地。竊以為禮學之要義在于不超脫經典的能自圓其說若,取折衷之言,實在是“取法乎其下”,不足為鑒。舉例來說,曾祖在“點主”條中詳細的記載了清代“點主”儀式,所謂“點主”,乃是在“發引”當日,“遷柩就舉”后延請身份顯貴之人將亡者事先準備好的神主(書例:皇清誥受某大夫某公諱某字某大人之神王)的“王”字上加一點。這一種儀式在清代極為盛行,但不知始作俑者為何人,此制古經全無,可以說完全背離喪禮本義,因此在《箋釋》中,我便做出如下說明:
此題主儀節殊為詳盡。古制,神主既成,只延善書者書主即可,然清代不知肇始何人,浸為書就之主,空其主上之點,喪家請顯官達貴或本族大賓于葬時點主,以示厚重,王氏《寧儉編》曰:夫主已書就,而獨留主字上一點,必邀請貴人于人子舉葬日,倉惶煩劇中補而足之,此亦何所取義乎?近來舊家故族,遲葬其親,甚至蹈水火盜賊之悔而莫追者,十九皆根于此等作俑淺夫,喜事鋪張,妄生枝節,造就此等繁縟儀節,而流俗相沿,并不知其奢而非禮。
當然,不可置疑,清代禮學的興盛在某種程度上是過去的學者們對經典的群體失憶或沉默造成的,但作為考訂的禮學是普世而絕非僅僅是埋首故紙堆的學問,家族祭祀便是很好的證明,“冠昏喪祭,蓋有家日用之體而通乎吉兇之需,固不可廢一而不講”。明清以來,關于家族祭祀的著述頗豐,禮學家們俱以所見,各記舊聞,如毛先舒的《喪禮雜說》、毛奇齡的《喪禮吾說》、王復禮的《家禮辨定》、許三禮的《讀禮偶見》、王心敬的《四禮寧儉編》、林伯桐的《士人家禮考》《品官家禮考》、張大翎的《時俗喪祭便覽》、趙執信的《禮俗權衡》以及朝鮮學者的《四禮便覽》《四禮釋疑》《四禮笏記》《常體便覽》《家禮集考》《喪禮備要》《喪祭輯笏》等,至于各宗族譜所載喪祭程序與條目,更是不盡枚舉。一方面,學者們素知禮學繁復,讓“蒙學之士開卷了然,倉促之間有所考據而無失”尚且困難,更何況讓販夫走卒、鄉野草莽之流本一家之說而通家祭精義,更需要反復揣測古經本義,有所發明。另一方面,家祭之學雖有朱子家禮與司馬書儀為藍本,但“確守家法無一言出入者甚鮮”,學者們為求蓋棺之論,讓天下各宗各家尊己之說而反復考索,左右征引,最終反而使得家禮之學無頭無緒,禮條混亂不堪。且清代家禮已拋離先秦“固所自盡”的基準,“今百姓送終,競為奢靡,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民俗多信僧侶誑誘,認為須世道輪回而大興水陸道場,斥巨資開堂找僧演劇,宴請賓朋,使民風凋零而失哀喪本義。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對曾祖的學問充滿著無比的敬重之意,這絕不會因我學識的不斷加深而稍有遞減。在《喪禮撮要》一書中,曾祖歸納了自己對禮經要義的理解:于心有安。例如他在“反哭”條中這樣寫道:
近俗于題主后即行安主,則不以靈車載主至墓所,故反哭禮多不行耳。若主載至山地,此禮定宜遵行,必待反哭后乃行虞祭。
虞祭雖曰安魂之祭,亦有慰于人心。凡葬,必奉神主反室而哭,日中而行虞祭,這一點,朱子有明確交代:“主人以下奉靈車在途行哭,至家哭,祝奉神主入,置于靈座……葬之日,日中而虞。”反哭禮不可或缺,清代定制,“既卜葬……題主、虞祭如常儀,歸奉升祔太廟”,由此可見,“必待反哭后乃行虞祭”是有根有據的。
又,曾祖在“卒哭”條中這樣寫道:
按古禮卒哭在虞祭后,今若能合三月之期而葬,則如古禮而行,然近俗多擇地而葬,三月之期甚有遲之數年者,將未虞而朝夕奠不罷乎?則失之煩。又有未卜佳城,或貧困不能久存,有不及三月之期,甚有數日即葬者。將既葬而虞,遂罷朝夕奠乎,則失之忍。茲酌過期而葬者,百日卒哭,罷朝夕奠,俟既葬而后行虞祭;不及期而葬者,葬畢,遂行虞祭,朝夕奠,至百日乃行卒哭,庶免煩與忍之失矣。
古禮,成服后行朝夕哭奠,至于士三月而葬,葬日即虞,卒哭乃在三虞后之剛日,所謂卒哭,即卒去“不時之哭”,改為朝夕“有時之哭”,以殺其哀之意,因此朝夕哭奠與卒哭不必再行重復。此本周代之禮,然而此制后世難以遵行,即作者交代,“近俗多擇地而葬”以至于數年不葬,又有家貧不及虞祭而葬,此皆明清以來實況,因為,作者便建議分兩種情況處理,若逾期未葬,則卒哭而罷朝夕奠,葬后即虞;若早葬者,則即行虞祭、百日后卒哭,這樣一來,就可以避免禮條擾人,也可以做到“心安理得”。
又,在“新主入祠祔祭合祀”條中這樣寫道:
《記》云:殷練而祔,孔子善殷,以不急于死其親。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茲酌祔主定于大祥之禮后行之,庶得孔程之意矣。
商在練祭即小祥后行祔祭,周在卒哭后行祔禮,因孔子乃殷之遺民,對殷禮自然有難以割舍的情結,故從殷禮,認為一年后而行祔祭,《開元禮》則認為禫祭而祔,程子認為大祥后一年而祔,蓋“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卒去不時之哭,又有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則不知哭所何處”。曾祖則認為,大祥后則中月而禫,禫祭名淡淡相安之意,似于人心更為安穩。因此在大祥之后將主入祠更為妥當。又,在“除神安靈致祭”條中這樣寫道:
按大祥之后,主即入祠,本屬至理,然今俗不以主入祠者,人人皆然。茲酌于大祥后除靈設祭,安主入家,亦不得已而為此也。
不過需要做出說明的是,雖然禮經繁復,清代許多學者都期望能夠“撮要而行”,在不失古禮愿義與便宜從事之間尋求一個較好的交點,但是本書在箋釋時,還是在某些條文與制度上詳細的交代了由來,以便于讀者對比勘合。例如,在“五服制度”條中,原文僅交代了五服之人各服之服,并沒有對每一服制的歷代演變做出詳細交代,在箋釋時,筆者做出了歷代服制沿革的補征:
斬衰三年:
子為親、養父母。〈周制,父在,則為母服齊衰杖期,父卒,為母服齊衰三年。唐制,皆服齊衰三年。明制,服斬衰。清制,服斬衰〉。若女未嫁、已許嫁者、被出而歸者,亦服斬衰。〈周、唐、明、清制為父則皆同,服斬衰。為母,明初服齊衰三年。后服斬衰。清服斬衰〉。父為長子。母為長子。子為繼母、為慈母、為養母、繼母〈周、唐、明、清制與母同〉、為慈母〈周、唐、明、清制與母同〉。庶子為所生母、為嫡母、適母。〈周制,父在,為生母服齊衰杖期,父卒則服齊衰三年。宋制,皆服齊衰三年。明制,服斬衰。清同明制〉、為嫡母、適母[周制,父在,為適母服齊衰杖期,父卒則服齊衰三年,明制,服斬衰。清同明制],子婦亦同。婦為舅、姑。〈周制,為舅、姑服齊衰不杖期。唐制,為舅服斬衰、為姑服齊衰三年。明制,為舅、姑服斬衰。清同明制〉。為人后者為所生父母服,子婦亦同。〈周制服齊衰三年。明服斬衰,清同明制〉。為人后者為所后祖父母,子婦亦同。〈周、唐、明、清制為后祖父則皆同。為祖母,周制服齊衰三年,明、清服斬衰〉。妻、妾為夫。〈周、唐、明、清制妻為夫、家長則皆同。妾于家長,古稱君,明稱主。清為家長〉。傳曰何以三年?夫至尊也,君亦至尊也。嫡孫為祖父母承重。〈周、唐、明、清制為祖父則皆同,服斬衰。為祖母,明增適孫之妻同,祖在為祖母服同。周制服齊衰杖期。明服斬衰,為高曾祖承重亦同,祖父俱亡。周、唐、明、清制為高祖父則皆同〉。為曾祖父母〈周制服齊衰三年。明、清服斬衰〉。
曾祖晚年生活在血與火的戰爭之中,但他仍舊能夠潛心做這種“過時”的學問,不管窗外如何炮火紛紛,他終其一生都沒有改變學問的方向,當然,最終也便不了了之。因為在那個年代,研究“民主”與“科學”、研究“”才是正途,否則皆視為妄作,被歷史證明為走不通的學問。歷史證明后者的確能挽救民族頹波,于今看來,似乎那些故紙堆的東西,對建設發展毫無益處。然而事實真正如此嗎?數十年前,人們認為“禮教吃人”,要“打倒孔家店”、祛除儒學“糟粕”,試觀今日之中國,德行淪喪、人心敗壞,此罪當咎于誰?人不講禮,類乎禽獸,我們丟棄了歷史的同時,也必將被歷史丟棄,這是亙古不變的一則道理,對于今日讀書人而言,過分追逐“現實意義”而忽視“歷史累積”,也同樣不可取。反過來講,曾祖生活在社會動亂的時期,尚能求學問之“放心”,而我現在生活在人心動亂的時期,為何不可也“求其放心而已矣”呢?
是書得以出版,自信功不唐捐,未來總會有大裨益于推治化之本。不過仍要感謝恩師宋玉波教授,先生早年赴英美諸國留學訪問,精通民主,在政治學界久負聲望、高風亮節,于我有知遇之恩;感謝臺灣中華大學行政學系曾建元教授,讓筆者有幸成為他主編的《中華人文社會學報》史上最年輕的作者,此書得以出版,也得荷先生向秀威出版社主編力薦;感謝肖云樞、曹麗兩位教授無微不至的關心,筆者對學問的諸多靈感,得益于兩位教授的耳提面命;感謝《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編輯部江雯教授,每念及江師的那句“沽之哉,沽之哉,以待識者也”,總能使我在內心喚起對學問的巨大驚喜;感謝夏雪老師,她總愿意靜心聽我傾訴我的潦倒困惑,為我的諸般困頓解惑答疑;感謝秀威出版社的楊宗翰、孫偉迪兩位編輯,感謝他們給予我完成曾祖心愿的機會以及在編輯過程中付出的辛勤勞動。
感謝愛人春香,從十余年前尚不諳世事的“點燈登閣各攻書”到今日的“移椅依桐同望月”,我能夠安心讀書作文,全仗于她毫無私心、怨言的照顧,本書的圖表編排也得益于她得指點。雖然我深知現在的學問尚不可使我安身立命,但十余年來,她始終堅信我終有一日能學有所成,假以時日,我當不辜負她的寄托。總而言之,沒有我的愛人,我的學問似乎也無從談起。
最應該感謝我的父母,孔子有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母,何有于我哉?”迄今為止,我尚不知“公卿”何在,依我的性格,也無心、無能、無意事之。十余年來,我四處游學,漂泊不定,亦未能陪伴在父母左右。父母垂垂老矣,但始終不忘記教誨我讀書的方法:學問之要,首在做人。
祭父范文第4篇
習俗:賽龍舟、端午食粽、佩香囊、懸艾、懸鐘馗像、掛荷包和栓五色絲線、點雄黃酒等。
故事:屈原愛國投江、伍子胥棄暗投明、孝女曹娥救父投江、古越民族圖騰祭、古越民族圖騰祭、五月五日是惡月惡日。
端午節,為每年農歷五月初五。據《荊楚歲時記》記載,因仲夏登高,順陽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個午日正是登高順陽好天氣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稱為“端陽節”。此外端午節還稱“午日節、五月節、龍舟節、浴蘭節、詩人節”等。
(來源:文章屋網 )
祭父范文第5篇
關鍵詞:孝;論語;孔子
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核心美德之一。其實,孝的思想早在孔子以前就已產生,在西周的銅器銘文之中“孝”字從老從子,象征老人扶子之行,象征年輕人攙扶族中老者。“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諸父諸祖亦應善事。”(《金文詁林》卷八) 在遠古的氏族和部落社會之中,“孝”的意義是很廣的,是指對本族中年長者的尊重、敬愛、贍養和祭祀[1]。隨著家庭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和社會長時間的發展,“孝”也由對族中老者的尊敬變成對父母的關愛,成為處理家庭內部關系的重要倫理規范,甚至在今天,對生者的“孝”更為受到重視。但是綜觀《論語》里的孝道思想,跟上古時期更為接近,那就是“孝”不僅僅是對父母的義務,還是忠于國家的品德基礎,是成為一個合格的士的標準之一,在孔子那里,孝不僅是物質上的供養,更是精神上的撫慰和祭奠。
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社會劇烈變動的時期,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必然引起傳統意識形態的動搖,在禮崩樂壞的社會狀況之下,傳統宗法社會中維持人際關系的孝道思想也受到了嚴重沖擊,子弒父、臣弒君的現象時有發生。在整飭社會秩序,重建孝道倫理的過程中,孔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孔子認為“孝”是一切道德規范的根本及其發展的前提。《論語》記載了孔子的學生有子所說的一句名言:“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也。”這句話是說,孝悌是做人的根本, 人之行莫大于孝, 為人者如果做不到孝, 那其他的品質也就無從談起。有子繼承的是孔子的思想,可是說這是對孔子孝道思想的延展,孔子自己也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凡愛眾,而親仁。行有馀力,則以學文。”在另一本儒家經典《孝經》中還有一句話說:“孝乃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儒家從理論上肯定了孝是人倫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強調為圣人的必要準則,而孝作為仁的內核,可見其地位之重要。有子認為“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犯上和作亂即為不忠,孝悌者鮮犯上而無作亂,是忠君愛國思想的擁護者。我們現在常說“孝順”一詞,似乎孝敬就代表著順從長輩或者權威的意志,那孝是不是就是愚忠和逆來順受?很多人因此產生誤解,批判《孝敬》的愚昧和保守。其實,僅就這一點,孔子早就給出了答案。有一次,曾子問孔子,“孝”是不是就等于“從父之令”,缺乏自己的獨立意志和價值的準則呢? 孔子的回答是:“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臣不可不爭于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在“孝”之外,孔子還用了另一個道德的準則“義”來規范它的實行。如果上級或者長輩言行不已,就可以阻止或者不執行。可以看出,“義”作為一個概念是超越了君臣、父子的倫理關系的,《荀子子道篇》記載了同樣的一段話。魯哀公問孔子同樣一個問題。子貢認為“子從父命”就是孝。孔子說子貢是“小人”。孔子指出“子從父”不能說子“孝”,臣從君,也不能說是臣“貞”。孔子說:“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總而言之,“孝”是子對為什么要從“父之令”的審慎的把握。把握的標尺就是“義”。“孝”由此就成為小輩或者臣子依據一種更高的價值目標和價值準則,根據一定的認識論方法處理與君和父的關系的一種品性。在這種解釋思路下,“孝”不是無原則的服從,“孝”是學道的表現和成就,是對自己內心最高價值準則的服從。“孝”不是對長輩和上級的單向的義務。
其次,孔子認為在精神上的孝,意義遠大于物質的供養。關于這一點,孔子在《論語》中多有論述,對于不同弟子的提問,他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是其中的要義都是一致的。他認為一般人所說的養就是孝的觀念是有問題的。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孔子認為,就是家里豢養的動物,都能在物質上被給予很好的照顧,那么給父母的物質供養就不足以成為孝與不孝的分界線。能夠區分的只有抽象的情感。所以色是難的,要做到面對父母的時候,不厭煩而有愉悅之色,并不是每個家庭都能做到的。如果整天擺著一副臭臉,父母就是天天食鮑魚吃燕窩也不會開心的,父母最需要的是心靈的慰藉。看到這兩句,心中感慨頗多,孔子的教導對現代人來說指導意義更大。在古代,交通不便,疆域窄小,出趟遠門并非易事,正所謂“父母在,不遠游”。但是今天,除了農村那些出不來的人,還有多少人愿意固守家園,守護自己的父母?的確很多時候,我們可能身不由己,繁忙的工作,又有誰考慮到父母的感受?每當我們推說加班加點而沒空探望他們的時候,我們是否記得孔子的教誨?那首《常回家看看》在大江南北的走紅不是沒有原因的,這一點,我很佩服孔子,他洞察到了人內心的想法,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癥結所在。在父母眼里,子女的陪伴和關切比物質的豐盛要重要得多。所以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是的,既然是孝子,那他在物質和言行上的態度就不會受到父母的微詞,唯有疾病,是天災,很難由人力控制,是父母和孝子都沒有辦法的。這種疾病,不是自身的不注意造成的。因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損毀。”所以自然的病癥成為父母也是孝子最無能為力和擔憂的事件。另外,孔子還說:“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皆弟之言。”對于父母對自己孩子的看法,向來都被認為有主觀的成分,但是人們不會對孝子父母對孝子的看法有懷疑和不好的評價。孝道作為人倫之一,那個時代是大家很重視并且有目共睹的,如果是公認的孝子,那么他的言行對社會就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成為道德楷模式的人物。此時,就連父母家人也變成了“孝”的監督者,他們的言行是有公心且可供參考的。由此可見,孝在當時已經被提升到了一個怎樣的高度。
再次,孝道對政治能夠起到作用。除了間接地從孝到忠,孝道還可以淳化社會風氣,教化大眾,安定社會。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孔子認為,在家族里對長輩的孝敬,對兄弟的愛護,可以維護一個家族的正常次序,這是有利于社會安定的,當然是為政的一個方式。孔子還解釋說: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在他看來,倡孝實際上就是一種用德行來影響政治,作用于社會與百姓,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治國方略。因此,孔子及儒家主張用孝教化百姓。“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孝經廣要道章》) 對人們“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 所以敬天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為人君者也。”(《孝經廣至德章》) 這樣社會就會穩定, 形成“ 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的局面。《孝經》可謂儒家經典,雖然直接吸收孔子的思想不多,但《孝經》對孝的思想的闡發可以說是繼承了孔子的傳統,又生發開來的。特別關于孝和政治的關系,很好地繼承了孔子的想法。先秦儒家孝道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使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在中國社會舞臺中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從漢以后“以孝治天下”的格局貫穿于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我認為,西漢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舉孝廉的政策應該就是儒家孝學說影響巨大的有力證據。舉孝廉之人,直接為官,看來孝真是與政治不可分割了。到了元明清時期,很多文人創作的戲曲和小說更是體現了用孝來教化大眾的思想傾向。比如《琵琶記》、《任孝子立地成神》等等。
最后,《論語》中提到,孝不僅是生養,還是死葬,不僅是對人生前的尊敬,更是對死后亡靈的尊重,慎終追遠,這才是孝的完結。比如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這里的“違”應指的是違背禮節。就是說不管長輩是否在世都必須按照禮節來侍奉他們。對于死去的人,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楊伯峻將“道“解釋為父輩合理的東西,引發了學者的爭議,有人認為,三年不改,難道超過三年就可以把合理的東西改掉嗎?我覺得這是鉆牛角尖,孔子說過,順從并不是孝,這里應當采取楊的解釋,即在父喪的三年之內,尊重父輩遺留下來的合理的教義,三年之后,可以添加或者根據具體要求進行修訂,但是對合理的東西至少保證三年的不變化。沒有什么對錯只之分,只不過時移事易,對待不同的事件一定有不同的正確防范。對于喪葬的禮節,孔子認為并不是越隆重奢靡越是孝。正如前面所說,孔子重視的是心,而非物質。同樣在論語中,他說:“禮,與其奢也,凝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儒家在強調“ 哀戚”的神色,必須是發自內心的憂傷,就是對死者最大的祭奠。同時,儒家又認為這種悲哀之情是有節制的。要“致乎哀而止”(《論語子張》) 要有三年之祭,“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但“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而對于喪祭之事,孝子必須恭敬嚴肅, 孔子說:“吾不與祭, 如不祭。”(《論語八佾》)“ 喪事不敢不勉”(《論語子罕》)表達了在祭祀時對先輩要虔誠。
可以看出,雖然在《論語》中,只有十九處明確地提到了“孝”,但是那些關于祭祀、關于忠、仁的闡釋也是跟孝不可分割的。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理解,“孝”乃是研究孔子甚至儒家思想繞不過去的一條重要線索,從《論語》到《孟子》、《荀子》和孝經,以及后世諸多的儒學經典,都清晰地記錄了“孝”的發展軌跡。無怪乎有學者認定,中國的文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孝的文化。當然在談到孝道的積極意義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過分絕對、片面地愚孝和死板遵守儒學教義對民族精神的傷害,對于每一種思想,我們都應當審慎和警惕,保持客觀的研究姿態。
參考書目:
(1)魯行經院學報范玉秋林雨 2002年第5期論《孝經》對孔子“孝”的思想的發展
(2)東岳論叢 2005 年5 月第26 卷第3 期黃開國先秦儒家孝論的發展與《孝經》的形成
(3)《孝經譯注》 汪受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4)《論語譯注》 楊伯峻譯注中華書局 1980年12月第2版
(5)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 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1 期 李淑霞論孔子思想中的誠信與孝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