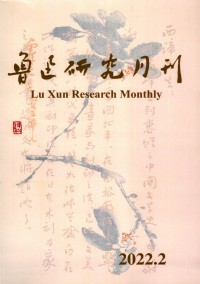穆旦詩八首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穆旦詩八首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穆旦詩八首范文第1篇
它渴求著擁抱你,花朵。
反抗著土地,花朵伸出來,
當暖風吹來煩惱,或者快樂。
如果你是醒了,推開窗子,
看這滿園的欲望多么美麗。
藍天下,為永遠的謎蠱惑著的
是我們二十歲的緊閉的肉體,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鳥的歌,
你們被點燃,卷曲又卷曲,卻無處歸依。
呵,光,影,聲,色,都已經(jīng),
痛苦著,等待伸出新的組合。
——穆旦《春》
這首詩寫于1942年,詩人時年24歲,正值想象力豐富的青春年齡。我們大都有過春天的經(jīng)歷,當你我來寫這一題材時,很可能就是寫春景,抒春情,盡力把春天美意表現(xiàn)出來,讓大家感到共鳴。在不少人眼中,春天就是萬物復蘇的開始,除了花草生長,我們能理解的更多還是一種抽象的季節(jié)。而春到了穆旦筆下,沒有了朱自清的恬淡優(yōu)雅,也無雪萊“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的尖利追問,他只是用異于古典的筆調(diào),寫下了對春的新奇之感。我們在很多關于春天題材的詩歌中,讀到的往往是一種散文化的抒情,但是穆旦力避此點:他寫春,沒有落到俗套里,而是充分發(fā)揮想象力,讓所有意象都在現(xiàn)代性的組合中得到了自然的安放。這要比那些依靠激情和沖動寫詩的人,更富智慧和說服力。
春天向上的力量,沖破一切束縛的魄力,都在穆旦的詩中得到了展現(xiàn)。它不是平鋪直敘的書寫,而是讓春天盡量變得真實。因此,詩人使用的一些修辭手法,是為了在節(jié)制中避免酸腐之氣。草生長得很旺盛,這是生命力強的象征,但詩人沒有這么寫,而是說“綠色的火焰在草上搖曳”。這種畫面感的凸顯,已不僅僅是在寫春了,而是在寫一種意境,這正是穆旦所要追求的現(xiàn)代詩歌美學。接下來的意象,像欲望、謎、緊閉的肉體、泥土做成的鳥的歌等,看似都與春天無關,其實它們又恰是詩人為寫春所敞開的想象之源。穆旦是在用一種陌生的意象組合,營造新奇和張力。第一節(jié)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能讀懂:詩人寫出了春天的動態(tài)之美。而在第二節(jié)里,詩人開始轉(zhuǎn)向精神對話,依靠靜態(tài)理性來認知世界。他將春天的力量,與一個人的青春期作了對比,這種對比更顯出了春作為新生力量的蓬勃朝氣。
除了《春》之外,穆旦還在晚年陸續(xù)以另外三個季節(jié)為主題,寫過《夏》《秋》《冬》。他以超越常規(guī)的姿態(tài),寫出了每一個季節(jié)在詩人眼中的真實,而滲透其中的美學,就是無處不在的現(xiàn)代意識。這種現(xiàn)代意識正是穆旦所獨有的特質(zhì),它反對空洞和概念化,既不過度抒情,也不以玄學表達來掩蓋邏輯的混亂。他在想象和經(jīng)驗的結(jié)合中自如地游走,一方面展示了現(xiàn)代漢語的美感,另一方面又給出了思想的力度。那種滲透在字里行間的哲思性與命運感,總能在不經(jīng)意間觸動我們,讓人真正領略詩人出其不意的創(chuàng)造力。
很多詩人到了晚年,少有能越過自己年輕時的創(chuàng)作,而穆旦是個例外。他以一種瓷實、綿密的哲思書寫,超越了自己,為我們留下了不少經(jīng)典之作。尤其那首《冬》,是穆旦接續(xù)上了青春時代的愿望,完成了對一年輪回的書寫,這也可以看做是他對自己人生的告慰:“我愛在冬晚圍著溫暖的爐火/和兩三昔日的好友會心閑談/聽著北風吹得門窗沙沙地響/而我們回憶著快樂無憂的往年/人生的樂趣也在嚴酷的冬天。”與春天相比,冬天更適合產(chǎn)生思想,那種嚴酷性能考驗人對這個世界的愛與擔當。冬天是對人生的總結(jié)之季,一切形象的事物,這時都會隨著理性的參與,而變得沉穩(wěn)、深刻,遠離喧囂,迎來思考,這是穆旦能一直堅守在詩歌現(xiàn)場的緣由。
對人生命運的思考,穆旦不僅將其置放在對季節(jié)的書寫里,有時,他更是直接把它當做某種思考的經(jīng)驗來處理。比如,他以具象寫抽象,《愛情》《友誼》《理想》《贊美》《奉獻》等詩作,都是詩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對情感、思考和愛的解讀,里面雖有不安、焦慮和無奈,但一種探索命運的想法,還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來,折射在那些文字里,暗示了詩人對其的向往和追求。像在經(jīng)典之作《詩八首》中,詩人建構(gòu)了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感性與理織,甜蜜與痛苦隨行,抒情主體展開了和命運的抗爭。有人說這是一首愛情詩,但在我看來,它是一首愛情與哲理交融的智慧之作,詩人在對愛的贊美中接受了愛情與生命終將消逝的現(xiàn)實,這也是他能以超然的心態(tài)對待命運的原因。愛情是詩人筆下永恒的主題,但讓純粹的愛情脫離肉體層面,上升到精神高度,又是穆旦《詩八首》成為經(jīng)典的關鍵。詩人沒有停留于表象的愛情描繪,而是通過深挖愛情之根來表現(xiàn)生命的哲理,賦予愛一種終極意義。
穆旦詩八首范文第2篇
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創(chuàng)作實際景觀,正是這樣。只是詩論者們還沒有加以發(fā)掘和總結(jié),反而得出抗戰(zhàn)時期沒有愛情詩的結(jié)論來。
一、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作
最先認為和時期沒有愛情詩創(chuàng)作的,是大詩人艾青。1980年3月5日,他說:“在戰(zhàn)爭年代,詩首先成了武器。詩人就成了戰(zhàn)斗員。情詩……為炮火讓路,――‘人面不知何處去’了。”同年8月,艾青又說:“炮彈不會談情說愛。”意思也是說戰(zhàn)爭年代不會有愛情詩創(chuàng)作。
隔不了幾年,新詩史論家、詩評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謝冕,也認為和時期沒有愛情詩創(chuàng)作。他有這樣的描述:“的炮火掩蓋了、驅(qū)走了戀人們的輕歌。人們在戰(zhàn)爭的烽煙中,陷入了國破家亡的深重災難。”“愛情詩開始了第一個零落季節(jié)。”“激昂的戰(zhàn)聲代替了個人情愛的悲歡之詠嘆。”“大概是時代過于嚴酷,我們連戰(zhàn)亂中的愛情悲劇的印痕也難覓到,更不說歡情曲了。”“三十年代后期直至四十年代后期,我們……留下了愛情詩的空白。”
艾青和謝冕這一與事實不符的觀點,后來居然被一些新文學史家攝取并擴大化為:“抗戰(zhàn)爆發(fā)后”,全部“情愛文學理所當然地進入了一個零落時期。在烽火遍地、國破家亡的災難歲月中,大眾的血淚和戰(zhàn)斗的吶喊,掩過了作家們個人情愛的發(fā)抒。……激昂的愛國熱情代替了兒女情長的詠嘆。”而寫進一部“以主題現(xiàn)象為中心構(gòu)建文學史框架”編寫文學史著作、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新文學史教材里去了。其影響范圍之大,自不待言。
事實并不是他們所說的那樣。且不說時期,也且不說愛情小說和愛情劇本,就只說時期的愛情詩創(chuàng)作,在筆者掌握在手的有限資料中就有下面這些:
《陜北情歌》,劉御(1912-,云南臨滄人)在延安作于1939年,同年發(fā)表于延安某報刊,收入詩集《延安短歌》,通俗讀物出版社1955年版,見于《新詩選》第三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烽火情曲》,嚴杰人(1922-1946,廣西賓陽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春,同年8月5日發(fā)表于《廣西日報?漓水》,收入詩集《今之普羅米修士》,桂林今日文藝社1941年11月版;
《櫻花曲》,鐘敬文(1903-?,廣東海豐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春,同年收入詩集《未來的春》,上海言行出版社1940年6月版,見于《中國現(xiàn)代新詩三百首》,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寄慧》,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在粵北坪石作于1940年11月15日,同年12月25日發(fā)表于《現(xiàn)代文藝》第2卷第3期,見于《穆木天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
《戀歌》,(1903-1987,廣東梅州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5月,同年12月5日發(fā)表于《中國詩壇》新6期,見于《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詩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奴隸戀歌》,何彬(1915-1941,湖北咸寧人)在湖北恩施監(jiān)獄作于1941年10月6日,發(fā)表于1942年11月3日《解放日報》,見于《新詩選》第三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獄中歌聲》,何彬在恩施監(jiān)獄作于1941年11月,見于《革命烈士詩抄》,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愛》,侯唯動(1917-,陜西扶風人)在延安作于1942年1月8日,發(fā)表于1943年1月1日出刊的《詩墾地》第4輯,見于《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詩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詩八首》,穆旦(1918-1977,浙江寧海人)在昆明西南聯(lián)大任教時作于1942年2月,收入《穆旦詩集(1937-1945)》,1947年初版,見于《新詩選》第三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姑娘》,陳輝(1920-1944,湖南常德人)在河北淶涿平原作于1942年春,同年發(fā)表于4月出刊的《詩墾地》第2輯《春的躍動》,見于《中國現(xiàn)代新詩三百首》,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訴》,嚴杰人在桂林作于1942年春,同年6月29日發(fā)表于《廣西日報?漓水》;
《戰(zhàn)斗情曲》,禾波(1920-,四川榮縣人)在重慶作于1943年9月3日,發(fā)表于1946年8月出版的《詩激流》叢刊第2期,見于《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詩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出版;
《毋忘我》,林林(1910-,福建詔安人)離開桂林到香港后作于1943年,收入詩集《同志,攻進城來了》,文生出版社1947年9月版,見于《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詩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春天和蜜蜂》,穆旦在昆明作于1945年4月,收入《穆旦詩集(1937-1945)》,1947年5月初版,見于《中國現(xiàn)代新詩三百首》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據(jù)說,七月詩派詩人鄒荻帆和長于愛情詩創(chuàng)作的阿垅,在抗戰(zhàn)時期都寫有愛情詩,但筆者未能覓到。
稍為涉及愛情的抗戰(zhàn)時期的詩作,如艾青的《火把》、鐘敬文的《今別離》等,都未計算在內(nèi),這里所列舉的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便有21首之多。僅穆旦一人便作有9首。抗戰(zhàn)時期“留下了愛情詩的空白”之說顯得理由不夠充分。
創(chuàng)作上列這些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時,年紀最大的是穆木天,他寫《寄慧》時40歲了;年紀最小的嚴杰人,他寫《烽火情曲》時才18歲。而且這里列出的他的兩首愛情詩,都是那樣出類拔萃、卓越超群,他真不愧為文學神童的稱號。抗戰(zhàn)期間,嚴杰人還有一首詩作《邱比得禮贊》,從題目上看,好像也是愛情詩,但筆者尚未見到這詩的正文,這里只能不加以評說。
這里列有作品的11位詩人,他們在抗戰(zhàn)時期的新詩流派歸屬各不相同。屬于延安詩派的是劉御、陳輝;屬于以艾青為最重要成員的七月詩派的是侯唯動、何彬;屬于中國詩壇派的是嚴杰人、鐘敬文、穆木天、、禾波、林林;屬于新現(xiàn)代派(九葉詩派)的是穆旦。由此可見,當時中國新詩壇上各個詩歌流派,或多或少都有各自的詩人參與了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創(chuàng)作。
二、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的特點
常言道:“國家不幸詩家幸”。在中國多災多難的時期,新詩的確取得了一次發(fā)展的機會,其中的愛情詩也取得了一次發(fā)展的機會。艾青在《論抗戰(zhàn)以來的中國新詩》一文中說過:“抗戰(zhàn)以來,中國的新詩,由于培植它的土壤的肥沃,由于人民生活的的艱苦和困難,由于詩人的戰(zhàn)斗經(jīng)歷的艱苦和復雜,和他們向生活突進的勇敢,無論內(nèi)容和形式,都多少地比過去任何時期更充實和更豐富了。”盡管艾青因為不關注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創(chuàng)作,只是從理念出發(fā)想當然地得出抗戰(zhàn)時期沒有愛情詩這一與事實不符的觀點,但以他對“抗戰(zhàn)以來”中國新詩的總體評估的精神來審視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創(chuàng)作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之處,還是合適的。
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其數(shù)量遠遠不如“五四”至抗戰(zhàn)以前那段時期的多。那段時期,不僅有散見于報刊和詩集的大量的愛情短詩,而且還有湖畔四詩人的《湖畔》(1922年)、汪靜之的《蕙的風》(1922年)、郭沫若的《瓶》(1925年)、李唯建的《影》(1933年)等一些愛情短詩集和愛情長詩集。然而,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的質(zhì)量之高和精品所占比例之大,與過去那段時期的愛情詩相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現(xiàn)在我們能夠見到的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雖然不過21首,但其中可稱之為力作、杰作乃至絕唱的,就有穆木天的《寄慧》、陳輝的《姑娘》、鐘敬文的《櫻花曲》、何彬的《奴隸戀歌》、嚴杰人的《烽火情曲》和《訴》,所占比例約高達三分之一。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有其獨特的特點:過去的愛情詩,往往局限在知識分子個人情愛悲歡之詠嘆上;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謳歌的對象,則拓展到了下層勞動群眾的愛情生活上。過去優(yōu)秀的愛情詩,充滿著反對封建主義的信息;抗戰(zhàn)時期優(yōu)秀的愛情詩,唱出了打倒帝國主義的最強音。過去的愛情詩,感情濃烈而思想力度稍為薄弱;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感情同樣濃烈而且更具思想力度了。
抗戰(zhàn)時期,穆木天夫婦都任教于中山大學,先從廣州遷往昆明,后又從昆明遷到粵北坪石。情深意切、語言平實的《寄慧》一詩,是穆木天在坪石寫給還滯留在桂林的妻子彭慧的。穆木天及其妻女途經(jīng)桂林同住于施家園一段時間,然后他又只身先期到達坪石。穆彭夫婦在桂林滯留期間,積極參與文化界的活動和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之余,還經(jīng)常和朋友們在家里談論國家大事,為國家擔憂。有一次,他們動容動情的議論,激動了經(jīng)常在旁邊聽大人議論的小女兒穆立立,她情不自禁地喊出了要上前線去打日本鬼子的口號。穆木天大受感動。這一作為穆、彭愛情結(jié)晶的愛女的舉動,詩人寫到了詩里:“如同朝霧籠罩在江上,/憂郁籠罩在我心里,/但如同太陽撕破江上的濃霧一樣,/我要用忿怒的戰(zhàn)斗的火,/燒破我的憂郁。/慧!請你叫立立大喊一聲嗎:‘爸爸!給我多吃一碗飯,/我一個人也要打日本鬼子去!’”這一結(jié)尾以幼童之語出之,卒章申志,韻味深長。全詩把夫妻愛情、父母親情與抗日救亡的愛國之志融為一體,讀之感人至深。“在月色里,/我渡過了琥珀色的湘江,/湘江之水真是美麗!/我想著這一道水流過你的家鄉(xiāng),/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鄉(xiāng)里。”詩中無一句直抒夫妻情意,而夫妻情意卻已融化在兩條江水的奔流里。穆木天是吉林人,故鄉(xiāng)有松花江;彭慧為湖南人,故鄉(xiāng)有湘江。詩人看到美麗的湘江流過妻子的家鄉(xiāng),想象著“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鄉(xiāng)里”,又由美麗的湘江聯(lián)想到祖國的錦繡河山“想到祖國的現(xiàn)在和過去”,并感嘆道:“祖國沒有得到解放和自由,/對著美麗的自然,/我永遠是感不到歡喜和安慰!”把夫妻情意開拓為對祖國對人民的厚愛。詩里有詩人早年倡導的主、客觀世界“交響”的余音,還成功地把象征主義的一些手法運用進去,增強了藝術(shù)表現(xiàn)的力度。毫無疑問,這是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的力作之一。
鐘敬文的《櫻花曲》,把詩筆刻畫的對象拓寬到國際領域更大的天地里,寫了戰(zhàn)時日本國土上發(fā)生的一個愛情悲劇,表現(xiàn)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發(fā)動的,也給日本人民帶來失去愛情失去幸福,造成深重災難的巨大主題。一個名叫若子的日本姑娘,在櫻花盛開時節(jié),懷念著她那到中國來送死在戰(zhàn)場上的情人。這首詩不僅在題材的選擇上有其獨到之處,在藝術(shù)表現(xiàn)上也很出色。它把“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那種“化我為他”的手法和魔幻主義的手法先后用到詩里去了。若子姑娘“對著霞彩般的櫻花,/她做起白日夢來了”。她看見在中國“那籠罩著死底氣味的原野上”的情人,“失神地在眺望,/眺望著他所來自的東方”,也就是他的日本故國。若子姑娘“本能地走前去,/那活著的年青人,/在不知道的瞬間/變成一具尸骸了,/口里仿佛還在低呤”,還以為他來送死是光榮的,真是死不覺悟。日本源于幕府時代的武士道精神流毒之深遠,于此可見一班。這也正是許多戰(zhàn)時日本姑娘失去愛情的時代原因的歷史內(nèi)蘊。詩的歷史感是深厚的。這是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中奇葩般的一首杰作。
革命烈士何彬的《奴隸戀歌》,如其小序所說:“奴隸們不是沒有戀愛,而是有著更熱烈更純潔的戀愛。”詩篇通過戀人“我”來探監(jiān)時對“你”的親密備至的關懷,暖人心窩的體貼和殷殷勉勵的生動描寫,把一對革命愛侶無比高尚、無比純潔、無比熱烈的恩愛感情,盡情地宣泄出來。悲壯的探監(jiān)畫面,以柔美凄婉的情調(diào)勾勒出來,給人以崇高悲壯的美學感受。
嚴杰人的《烽火情曲》發(fā)表在《廣西日報?漓水》上時,只是詩的第二段,全文于1941年6月20日發(fā)表在《中學生(戰(zhàn)時半月刊)》第44期。第一段刻畫了一個柔情似水般可愛的農(nóng)村姑娘形象。她對著出征抗日正在前方為保衛(wèi)祖國而戰(zhàn)的情哥,唱出了纏綿深情的思戀之歌。和《烽火情曲》一樣堪稱絕唱的,是嚴杰人的另一首愛情詩《訴》:
一
“我是一個求乞者/你是一個施與者/我是那樣謙卑/你是那樣慷慨”
“我才是求乞者/你才是施與者/是我謙插/是你慷慨”
“不/我們互相求乞/我們互相施與”
二
“在地愿為連理枝”/我們用愛纏在一起
“在天愿作比翼鳥”/我們張開翅膀/向著光明/一起飛呀飛
嚴杰人學習民歌和古典詩歌,有他自己的特點和美學追求。他不像劉御及其《陜北情歌》等延安詩派詩人及其民歌體詩作那樣,連民歌的句式言數(shù)也注重學習。嚴杰人則是撇開民歌的句式言數(shù),而重在學習其表現(xiàn)技法。《烽火情曲》和《訴》,都運用了民歌的對唱格式,卻不受民歌對唱格式兩句對兩句或四句對四句輪番對唱的局限。《烽火情曲》只用了對唱格式;《訴》第一段一、二兩節(jié)是對唱,第三節(jié)是合唱,第二段又以合唱的形式出現(xiàn),顯得靈活多變。
中國歷史上男尊女卑觀念造成女性受教育程度低下,女性知識分子少得可憐,致使有些女性只要略具少許文化或稍有一點姿色,便自以為是了不起的驕人資本。因此,婚戀中的青年男子往往成為愛情的“求乞者”,對方則成為愛情的“施與者”。這是在愛情與婚姻問題上表現(xiàn)出來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
思想深刻、觀察細致、感覺敏銳的嚴杰人,對這種不平等的愛情,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他主張愛情雙方應該是平等的。他希望青年男女的愛情,既是“互相求乞”又是“互相施與”的愛情。《訴》一詩,形象生動地表現(xiàn)了男女雙方,在愛情問題上由認識不一致到認識一致,再到行動一致的詩意流程,寫得詩意盎然。
三、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的影響
“五四”時期“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湖畔四詩人,其愛情詩成就最高的汪靜之,于1979年回憶說:“湖畔詩人把情人看成對等的人,彼此之間是平等關系,詩里只有對情人人格的尊重。”“對情人人格的尊重”,并不一定就能說明“彼此之間是平等關系”。那時期,汪靜之有一首題為《不能從命》的愛情詩,首節(jié)這樣寫道:“我沒有崇拜,/我沒有信仰,但我拜服妍麗的你!/我把你當作神圣一樣,/求你允我向你歸依。”此詩收入《蕙的風》。詩中描寫的男子形象,就是一個“謙卑”的單方面的“求乞者”的角色。
“我必須是你身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這是出自舒婷愛情詩名作《致像樹》的警句。讀者大都耳熟能詳,發(fā)表在1979年《詩刊》第10期的這首詩(寫于1977年3月27日,當時作者25歲),頗為引人注目,好評如潮,至今盛名不衰。《詩刊》副主編、編審、詩評家朱先樹說:“舒婷的《致橡樹》,由于所表現(xiàn)的是一種打破尊卑的勇敢,追求人的自我價值平等而受到普遍的歡迎。”著名詩評家謝冕說:“在愛情與婚姻受到嚴重污染的今日,舒婷這首詩否定了愛情的依附關系”,表現(xiàn)了“這詩的主人公”“對于獨立的愛情和生活的渴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詩評家吳思敬還評論道:“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女人被封建的綱常禮教壓在最底層,女性的獨立人格被極大地扭曲,形成了對男人的根深蒂固的依附心理”,“這種心理即使到了現(xiàn)代社會也仍然有強大的市場。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舒婷發(fā)出了振聾發(fā)聵的呼喚”,是“新時期女性人格獨立的宣言”,“這無疑體現(xiàn)了女性意識在新時期的覺醒與張揚”。這些評價是相當高的了。然而,晚了25年才面世的《致橡樹》,其思想藝術(shù)境界,并未達到《訴》的水平。
創(chuàng)作于抗戰(zhàn)時期的《訴》一詩,其第二段首節(jié)“‘在地愿為連理枝’/我們用愛纏在一起”,令人想起民間情歌“入山看見藤纏樹/出山看見樹纏藤/樹死藤生纏到死/樹生藤死死也纏”;末節(jié)“‘在天愿作比翼鳥’/我們張開翅膀/向著光明/一齊飛呀飛”,則更令人想起《駕新郎?別友》一詞的結(jié)尾:“重比翼,和云翥。”兩者都把昂揚的革命激情和兒女柔情融洽地糾合起來了,給人以渾然一體的深切感受。全詩寫得這樣深入淺出,這樣意境高遠。那即使是較為杰出的詩人,也難以做到。
作為九葉詩派代表性詩人的穆旦,他寫于抗戰(zhàn)時期的9首愛情詩,時代色彩最為淡薄,從字面上看,不能判斷它們是寫于抗戰(zhàn)時期,經(jīng)現(xiàn)代派詩歌鑒賞行家講解,仍然嗅不到它們的時代氣息。因為詩中用以表現(xiàn)其思想的,是人們大都不習慣的所謂“戲劇化”等現(xiàn)代派手法,讓人感到十分難懂。“穆旦的《詩八首》是一組有著精巧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而又具有深厚的哲理內(nèi)涵的情詩。全詩以‘你’、‘我’和代表命運和客觀世界的‘上帝’三者之間的生息消長的沖突推動著愛情和生命過程的發(fā)展為線索,展開各種矛盾斗爭,并且由此構(gòu)成張弛有度的內(nèi)在節(jié)奏和渾然一體的戲劇性情境。”盡管有九葉派詩歌鑒賞行家作出如此解釋,也還讓多數(shù)讀者對原詩感到朦朦朧朧,如墜五里霧中,有人說它們表現(xiàn)了愛情沒有永久性。
總之,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應該在中國新詩中占一席之地,后來的詩評家中,有人說它們哲學內(nèi)蘊深厚,而藝術(shù)性更是高得不得了。其實“詩無達詁”,見仁見智,各自評說去吧。
參考文獻:
1、艾青《和詩歌愛好者談詩――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艾青談詩》,花城出版社,1982。
2、艾青《中國新詩六十年》,《艾青談詩》,花城出版社,1982。
3、謝冕《永不衰老的戀歌――論現(xiàn)代愛情詩》,《中國現(xiàn)代詩人論》,重慶出版社,1986。
4、馮光廉等《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5、馮光廉等《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編后記》、《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
6、馮光廉等《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7、轉(zhuǎn)引自龍泉明《中國新詩流變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穆旦詩八首范文第3篇
關鍵詞:海子詩歌;陌生化;技法
中圖分類號:I207.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0-0122-03
海子作為我國著名現(xiàn)代詩人,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更加強調(diào)對于新鮮事物的體會,突出不同事物在觀賞者眼中的質(zhì)感,強調(diào)詩人心中情感。陌生化是海子詩歌中最常見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已經(jīng)成為海子詩歌的特點。陌生化一詞首次提出是在20世紀初的俄國文學創(chuàng)作中,主要是希望改變?nèi)藗兩畹膯我恍裕屓藗儗τ谛迈r事物重新獲取興趣,真正體驗生活百態(tài)。什克洛夫斯基強調(diào):“藝術(shù)的目的是要人感覺到事物,藝術(shù)的技巧就是使對象陌生,使形式變得困難,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間長度,因為感覺過程本身就是審美目的,必須設法延長[1]”。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使用陌生化技法,能夠提升詩歌內(nèi)涵,拓寬詩歌表現(xiàn)形式,培養(yǎng)讀者文學審美能力。海子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已經(jīng)將陌生化技法運用靈活,充分表現(xiàn)出海子精神世界。
一、海子簡介
海子原名為查海生,出生在我國安徽省,是我國80年代中期著名的詩人,海子是在進入北京大學校園后開始的詩歌創(chuàng)作,由于海子特殊的精神世界,最終在1989年,海子選擇臥軌自殺的方式結(jié)束其一生。海子僅僅創(chuàng)作了7年的詩歌,但是卻為人們留下大量優(yōu)美的詩歌,例如《亞洲銅》《夜色》《祖國(或以夢為馬)》《春天,十個海子》《黑夜的獻詩》《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等等。
海子詩歌的創(chuàng)作特點就是能夠帶領詩歌欣賞者走入海子精神信念中,了解海子所想要表達的永恒情感。海子在詩歌中實際將永恒表現(xiàn)具體化,讓人們對于生命本質(zhì)深度探究,海子詩歌為詩歌欣賞者營造出來一個海子眼中的生命本質(zhì)情境,讓人們能夠眺望遠方[2]。
海子的詩歌全部都是抒情類文學作品,對于生命中所有的事物都表現(xiàn)出了海子所特有的情感,在對海子詩歌欣賞中可以發(fā)現(xiàn),海子詩歌是思想角度分析,海子是一個思想矛盾體,不僅僅能夠?qū)⑹澜缰械氖挛锞唧w性表現(xiàn),還能夠?qū)⑹挛锢寺挕懸饣?/p>
二、陌生化技法生活反常化
陌生化技法在實際使用中就改變了人們對于文學作品傳統(tǒng)的觀念,強化了對人們精神世界的影響,人們只要在欣賞文學作品時,就能夠為陌生化的文學作品所影響,最終于潛意識中沖擊人們慣性的思維[3]。
海子詩歌就能夠很好說明這一觀念的。詩歌是詩人為讀者提供的一個藝術(shù)氛圍,更是詩人眼中的世界。海子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非常明白陌生化的重要性,因此海子詩歌為人們展示的是海子精神世界,并不是直接告訴人們一些人生道理。在海子的詩歌中為人們營造了一個春暖花開的世界,人們在詩歌欣賞中都能夠?qū)硐胫械氖澜缬幸粋€新認識。在別人眼中未來的生活可能是迷茫的,但是在海子眼中未來卻是一個能夠創(chuàng)造幸福的遠方。在海子詩歌欣賞過程中,迷茫的人們對于未來生活有了新的動力,更加愿意探索生命中的美好,了解生命的真諦。海子詩歌中所描述出的未來生活,在人們眼中是那樣熟悉與陌生,幫助人們潛在的理想浮出水面,讓人們對自己有了重新的認識[4]。
詩歌是這樣,生活更是這樣。人們都能夠?qū)ι钣兄迈r的認識,推動人們甚至是整個社會的進步,就像人們厭倦了傳統(tǒng)的詩詞后,就有了詩歌。特色是一件產(chǎn)品被人們所熟知的基礎,陌生化是人們精神世界中的一種特殊性表現(xiàn)形式,也成為了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核心技法。
三、海子詩歌中陌生化技巧表現(xiàn)
海子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無形的將陌生化巧妙融入其中,讓海子詩歌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陌生化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一種技法形式,能夠讓人們對于已經(jīng)熟悉的事物有著全面的認識,人們對于事物重新感覺到新奇,增加文學作品美感。
(一)異化現(xiàn)實
異化現(xiàn)實在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中使用陌生化技法的直接性原因,陌生化已經(jīng)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中突出性的表現(xiàn)形式。
1.決絕后的坦白
海子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重來就沒有停止過對生命本質(zhì)的探索,在詩歌中更是將這種想法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海子在詩歌中將生命本質(zhì)抽象化的表現(xiàn),同時將人類對于自身的認識再次帶向一個新高度。物質(zhì)生活對于人們生活影響逐漸增加,人們在人際交往中更加關注物質(zhì)生活水平,道德倫理已經(jīng)發(fā)生了異化。海子對于人們精神世界的改變感受深刻,創(chuàng)作出了“我要做遠方的忠誠的兒子,和物質(zhì)的短暫情人,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這樣的詩歌,表現(xiàn)出海子在尊重每個個體獨立物質(zhì)需求的同時,努力保持自身生活需求,厭惡與其生活在同一個空氣中的想法。在人與人不斷接觸中,人們逐漸忽視對于人性的關注,往往在他人身上找到自身生活的價值,在個體無法確認自身價值時,就會陷入深深的迷茫中[5]。
在海子詩歌中可以明顯感受到社會生活對于人們的影響,海子批判了人們在生活過程中受到客觀因素的改變,逐漸忽視自身價值,個體不斷異化。社會在建設過程中為人們提供豐富物質(zhì)需求的同時,對于人們精神世界也是一種束縛,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逐漸失去了自身特性。海子的詩歌就能夠直觀反映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變化,以及海子對于這種變化的無奈。
2.反叛中的保留
海子對于生命本質(zhì)解剖中,對于人的內(nèi)心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了解中經(jīng)常需要直接面對生命中丑陋的一面。海子對于生命本質(zhì)探討中,更是無法躲避生命丑陋一面的問題,但是海子厭惡生命中丑陋的一面,同時還承認生命丑陋能夠促進人們精神世界的建設,正是人們擁有了生命丑陋的一面,才可以讓人們對于自身有著更徹底的認識,才能鞭策人們不斷向前、向上。
在海子的詩歌中,對于生命丑陋可以說是最大化的夸張,海子甚至寫出了“光明的景色中,嘲笑這一野蠻而悲傷的海子”這種詩句。丑陋的世界創(chuàng)作出丑陋的文學作品,但是人們在丑陋的社會中,還存在異化性的心理,也是海子詩歌所想要為人們所表現(xiàn)出的、他的精神世界。海子詩歌就是以這種異化的特點所被人們了解,在海子《秋日黃昏》中曾經(jīng)寫道“從此再不提起過去,痛苦或幸福,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這種詩句,表現(xiàn)出現(xiàn)實生活中每天所需要面對的痛苦或幸福,用更加清醒的頭腦生活[6]。
3.沉淪里的依戀
海子詩歌是有大量對于現(xiàn)實生活批判性的詩句,但是主要還是對生命的歌頌,探索生命的真諦。就如海子所說的“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種對于未來生活美好的暢想,這是海子在凡俗生活中對于生活的依戀。這種依戀是海子精神世界中無形的表現(xiàn),是海子眼中的未來世界。海子更加關注對于人們心靈變化的了解,對詩歌創(chuàng)作中明確自身創(chuàng)作風格,需要詩歌對人們帶來的情感。
在海子創(chuàng)作詩歌中,海子也在不斷對自身成長進行反省,了解自身想法,進而創(chuàng)作詩歌。海子詩歌可以說是海子精神世界及自我認識的集中體現(xiàn),在自我認識過程中,海子最為明顯的就是在反省中具有反叛精神。文學創(chuàng)作雖然提倡多元化共存,但是最終還是希望文學創(chuàng)作回歸到人性中,探索人的價值,了解生命的意義,面對現(xiàn)實生活的無奈。海子在自身反省中也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迷茫,甚至是自我否定的時刻,例如海子在《九月》中就曾寫到“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我琴聲嗚咽,淚水全無”。在對海子詩歌分析中應該了解海子詩歌中的陌生化技法,關注海子關注的對象[7]。
(二)海子詩歌中陌生化表現(xiàn)
在海子詩歌欣賞中,人們經(jīng)常能夠發(fā)現(xiàn)海子詩歌的特點,能夠有效說明海子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的才能。海子通過對于生命真諦的探索,為人們營造了一個海子眼中生命的真諦,讓人們對于生命有了全新的認識。
1.言說策略
任何文學在創(chuàng)作中都是人們語言作用下的成果,語言已經(jīng)成為人們生活交往重要的工具,基于語言交往的交際關系更加局限,正是由于交際關系的局限讓人們對于陌生化有了重新的認識。
海子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經(jīng)常通過第三方的言語將海子所想要表現(xiàn)的情感表現(xiàn)出來,例如海子在《麥地與詩人,詢問》中就寫道“你不能說我一無所有,你不能說我兩手空空”。人們在欣賞海子詩歌中,會在無形中進入海子為人們營造的環(huán)境中,用海子的語言表現(xiàn)出海子對于這個世界的不滿,對于這個世界的吶喊。言說策略能夠緩解人們在詩歌欣賞過程中的語言障礙,讓人們對于語言表現(xiàn)形式有著新的認識,豐富人們精神世界[8]。
2.審美觀念
海子詩歌中為人們營造出了一個人們所沒有想象到的世界,讓人們更加關注生活中的美感。海子詩歌用文學審美重新審視這個社會,在海子眼中社會應該是平和、安寧的,人們都能夠在每天生活中感受生活,對于自身有著重新認識,感受生活中的點滴快樂。人們的精神世界本來就不應該用外界的因素進行約束,應該在精神社會中無拘無束活動。在人們對于社會感覺到迷惘的過程匯總,海子對于這個世界全新認識,將生活中的美好盡情放大,讓人們重新認識到生活的意義,探索生命的真諦。
3.創(chuàng)作技巧豐富
海子對于生命及自身都有了重新的認識后,會選擇一種自身認為最適合的情感表現(xiàn)形式,因此海子選擇了詩歌,也可以說是詩歌選擇了海子。海子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使用了大量的文學創(chuàng)作技巧,讓人們對于海子精神世界有了全新的認識,了解海子詩歌中所想要表現(xiàn)的情感。陌生化技巧豐富了海子詩歌創(chuàng)作途徑,讓海子詩歌創(chuàng)作更加豐富,也豐富了人們對于自身的認識,觸動人們探索生命真諦的想法,同時為人們呈現(xiàn)出不同的海子[9]。
四、結(jié)論
本文對于陌生化技法在海子詩歌中進行簡單分析,了解海子詩歌創(chuàng)作中使用陌生化技巧的特點,了解陌生化技巧在海子詩歌中的表現(xiàn)意義。
參考文獻:
〔1〕什克洛夫斯基.藝術(shù)作為手法[A].內(nèi)布拉斯加大學出版社,1956.127.
〔2〕申瑋.“玄學詩人”約翰?鄧恩詩歌中的“陌生化”技巧[J].湖北科技學院學報,2015,(06):79-81.
〔3〕王紅濤,武娜.形式主義批評理論視域下看古詩中“陌生化”技巧的運用――以“詩鬼”李賀為例[J].海外英語,2015,(13):182-183.
〔4〕陳燕.蘊含在混亂表面之下的意蘊和諧――論卡明斯“古怪的印刷體式”詩歌的“陌生化”技巧[J].太原大學學報,2011,(02):61-63.
〔5〕趙志.論穆旦詩歌語言的陌生化技巧――以《詩八首》為例[J].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009,(01):19-20.
〔6〕肖曼瓊.“陌生化”:從詩歌創(chuàng)作到詩歌翻譯[J].外語教學,2008,(02):93-96.
〔7〕歐艷玲.論約翰?鄧恩愛情詩中的陌生化現(xiàn)象[J].重慶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學報,2008,(05):8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