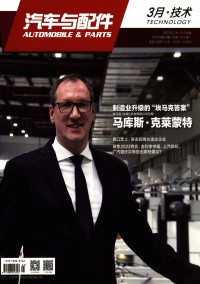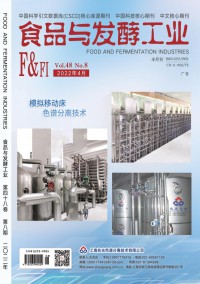莎士比亞的作品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莎士比亞的作品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莎士比亞的作品范文第1篇
摘要 “戲劇反諷”在莎士比亞劇作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使得他的戲劇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本文從兩個方面來論述莎士比亞作品中造成“戲劇反諷”效果的手段,以揭示莎劇“戲劇反諷”所具有的巨大魅力。
關鍵詞:莎士比亞 戲劇反諷 手段 技巧
中圖分類號:I106.3 文獻標識碼:A
一“戲劇反諷”的含義
“戲劇反諷”也有人稱“嘲弄”或“揶揄”等,是戲劇及其他文字樣式常用的手法。關于戲劇反諷的定義,在莎士比亞評論中也提到過。各類百科全書、文學詞典也有專條解釋。但是這些評論和解釋都有些片面。而在中國,無論是在對莎士比亞的戲劇進行評論的作品中,還是在對我國自己的傳統戲曲、現代話劇進行評論的作品中,都極少提及“戲劇反諷”這樣的概念。因此,在這里有必要就“戲劇反諷”進行說明。
《百年版布留沃文學詞典》對“戲劇反諷”的解釋是:“有觀眾領會舞臺上某個場景或某句話的含義與意思而劇中人卻沒有領會”。即“觀眾知道,劇中人不知道”,但是在有些時候“不知道”的并不是在臺上的全部劇中人,而是其中的一個或幾個,而在這種場合,“戲劇反諷”的效果往往更明顯,更強烈。伏恩(Vanghn)的《戲劇手冊》對“戲劇反諷”的定義進行了改進,他認為,“戲劇反諷”是:一種戲劇技巧,它使觀眾擁有劇中人物所不知道的知識,因此,觀眾們便覺得有時比劇中人物更加高明,他們能看出某一行動的含義而劇中人物卻不能。
他們的價值在于不但指出了“戲劇”特征和適用范圍,并且指出了戲劇反諷的兩種不同的功用。盡管上述定義都各有不足,他們卻都地提到了“戲劇”最基本的特征:劇中人的不知與觀眾的知,這種戲劇性在觀眾中產生反響,才能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和興趣,讓他們有耐心有興味地從頭看到尾,因此,“戲劇反諷”的核心就是知與不知的對立與沖突。“戲劇反諷”的手法可以用在喜劇中,也可以用在悲劇中,但作用是不同的。在喜劇中,它能造成誤解、身份誤會,以及混亂;在悲劇中,它可以使在臺上演出的不愉快的事件更為可怕。
二莎氏作品中造成“戲劇反諷”的手段
莎士比亞作品中的“戲劇反諷”,都是通過劇中人物的不知或無知兩個方面表現出來的:其一是對另一或另一部分劇中人物的身份的無知,由此導致“身份誤會”,其二是對他們本人所處的情境的無知,由此產生“情境誤會”。
1用“身份誤會”來表現“戲劇反諷”
所謂“身份誤會”,就是因某種原因認錯了或沒有認出人,在舞臺上常常可以造成十分滑稽可笑的場面。“身份誤會”也可以由純粹的無知造成,而手法豐富多彩。
用“身份誤會”來表現“戲劇反諷”,在西方戲劇(特別是喜劇)中是有傳統的,造成身份誤會的一套手法也為人們所熟知。所以在莎戲中比較醒目:如劇中人物的改頭換面,甚至改裝成另一個人。盡管在該劇本的故事中或許就有改裝一事,但對觀眾來說,這種手法的人為性還是較清楚的。姆韋克在論“諷刺”時指出:“在劇院里沒有比身份誤會造成的諷刺更常見的現象了”。
莎士比亞戲劇的創作中,“身份誤會”比較常見的形式為“偽裝”、“男扮女裝”這兩種形式。它們使莎士比亞的戲劇自成一格,在其他的作品中突顯了他的魅力所在。
(1)“偽裝”在莎劇中的出現頻率很高。不過,人們談到莎氏的“偽裝”總把注意力放到異性人物的身份變換上。其實在相當一些劇中,同性劇中人的改裝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例如他著名的悲喜劇《一報還一報》,維也納公爵為了重整綱紀,把權利交給了他的助手安哲魯,自己說是出游去了。可實際上,他把自己打扮成教士模樣,在暗中查訪民情,整個戲除了開頭和結尾,公爵全是以教士身份出現。這不僅使他有機會了解到底層人民的痛苦、高層官吏的腐敗,也使他卷入了一些十分滑稽可笑的場面,有時不得不聽別人講他壞話。
比如在第三幕第二場,公爵在監獄門前遇見了路西奧,兩人談起了公爵。在兩個人的對話中,路西奧對公爵說“……他(公爵)自己也是喜歡逢場作戲的”,還說到了公爵喜歡玩女人,在這種情況下,公爵只能是無可奈何。他只說了句“這我可不信,因為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說些什么話,可是公爵倘使有一天回來……我要請你當著他的面回答我的問話。”一個是不知道對方是誰在指著鼻子罵,一個是有苦難言,強作笑容,不過還算是為后面的結尾埋下了伏筆,產生了像這種妙趣橫生的場面。莎士比亞在悲劇、悲喜劇,甚至歷史劇中也要見縫插針地用上幾招“偽裝”,用它來解決矛盾和問題。
(2)莎士比亞運用“女扮男裝”技巧也很有特點。莎士比亞的天才技巧不僅表現在他對“偽裝”法的運用上,更表現在他通過“女扮男裝”塑造起來的戲劇形象,及好多舉世文明的戲劇大作之中。《威尼斯商人》、《皆大歡喜》、《第十二夜》,都是莎劇運用這種手法的珍品。
《威尼斯商人》中的鮑西婭為支持丈夫、救助朋友,裝扮成年輕的法官,在法庭上擊敗了狡詐的夏洛克。她的才華、氣度,都在這里表現得淋漓盡致。可是鮑西婭的男裝及他們的對話不但擊敗了夏洛克,而且使法庭氣氛不再那么嚴肅。反倒使戲劇變的幽默滑稽。
在法庭上兩位年輕女子也戲弄了各自的丈夫一番,使整個戲得以在喜劇中結尾。莎士比亞在劇中對戲劇反諷的運用,遠遠不止這些。除了在一些十分明顯的地方可以覺察到莎士比亞是用了“戲劇反諷”以外,還有很多時候,它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中運用的,因此顯得十分自然妥帖。但在一些劇作家或細心的觀眾心里,它們卻沒有被忽視。因為往往正是這些細小的場面,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2用“情境誤會”來表現“戲劇反諷”
莎士比亞在他劇作生涯的開端寫了一系列以歷史事件為內容的戲,一部分是以英國編年史為藍本的,另一部分則主要取材于古代羅馬的歷史,在大部分這樣的作品里,莎士比亞把歷史上,特別是英國歷史上的動蕩、戰亂搬上了舞臺,王公貴族明爭暗斗,爾虞我詐,有政治舞臺上的周旋,也有軍事戰場上的拼搏,這些內容,恰恰為情境誤會的設計提供了素材。
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中,造成“情境誤會”的手法并不只限于設計,有時候,劇中人的單獨的“無知”也是使他對某一情境產生誤會的原因,所謂單獨的無知,并不是因為有人設下了計謀而他不知道,只是簡單地對某個事件沒有足夠的了解,因而做出了與目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事。
當然,莎士比亞的種種“設計”、“無知”,其實都是歷史事實,但是戲劇家所做的其實不僅只是把史實改為對話直接搬上舞臺,他要做大量的藝術加工與修整,使它能上演,能吸引觀眾。莎士比亞也是對這些事實是經過加工剪裁后才搬上舞臺的,而正是他的這些改編,才把莎士比亞同別人區別開來。他的“戲劇”能巧妙自然地把歷史事實與戲劇手法結合起來,使人看去讀來并不覺得有人工斧鑿過甚之感。
在莎士比亞的五、六個劇作中,戲劇反諷幾乎支配了全劇的發展,它貫穿在全劇結構之中,例如悲劇《奧瑟羅》,悲喜劇《一報還一報》,喜劇《錯誤的喜劇》、《皆大歡喜》和《第十二夜》等,其中大部分是其作品的精華。當戲劇反諷支配故事情節發展并貫穿于全劇時,在所有的重場戲中,戲劇反諷都起了決定性的,或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在莎劇中還有很多劇,雖然在其中大部分場次中沒有運用戲劇反諷,或沒有以戲劇反諷為中心展開的情節,可是它們的重場戲中,戲劇反諷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這樣的劇情往往出現在“突轉”、“復雜化”、“結尾”處。在莎士比亞作品中,戲劇反諷在這些戲劇中的運用也是相當成功的。
莎士比亞作品博大精深,數百年來人們對莎劇津津樂道、贊嘆不已。莎劇之所以受人歡迎并具有無窮的魅力,“戲劇反諷”的運用在莎劇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莎士比亞在自己的劇本中為各類人物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臺,讓人物的善與惡,美與丑的交鋒在這個舞臺上通過“戲劇反諷”充分的展現。他塑造的人物,展示的情節不管是那種體裁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莎劇已經成為西方戲劇史上的高峰。
參考文獻:
[1] 李偉民:《中國莎士比亞戲劇研究綜述》,《國外文學》,1997年。
[2] 莎士比亞,朱生豪譯:《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國對外經貿社,2000年。。
[3] 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戲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又重新修訂定名為:《莎士比亞全集》。
[4] 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八、九),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
[5] 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上海圣約翰書院學生最早用英語演出,1902年。
[6] 施咸榮:《莎士比亞和他的戲劇》,北京出版社,1981年。
莎士比亞的作品范文第2篇
Feng Hong
(Weinan Teachers University,Weinan 714000,China)
摘要: 文學版本是文學譯本的基礎,也是文本研究的基礎。當前中國,對莎士比亞研究中的版本包括國內注釋本,以及中譯本研究方面還存在不足,應當引起莎學研究者的關注。
Abstract: Version of the literary text is the foundation of its translated vers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ext study as well. In modern China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its version, translated edition and annotated version, which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pay much attention to.
關鍵詞: 莎士比亞 中譯本 版本與注釋本
Key words: Shakespeare; Chinese version; edition and annotated version
中圖分類號:G41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14-0304-02
0引言
莎士比亞作品登陸中國大約已經有近170年的歷史,在這170年間,中國的幾代學者不遺余力地把莎士比亞作品以各種形式翻譯成中文,讓莎士比亞在中國生根成長。在當代中國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仍然是一個焦點問題,而且對于翻譯所依循的版本非常重視,除此之外,莎士比亞作品的注釋在當代中國也有相關書籍出版。無疑這些成果讓莎士比亞在中國的研究有了更為堅實的基礎。但縱觀目前莎氏的版本注釋本及譯本在中國的現狀,還有不少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1中國莎士比亞研究中版本與中譯本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對于文學文本的翻譯來講,版本的選擇是一個重要問題,一直都受到足夠的重視。版本質量直接影響到譯文的整體美學效果,乃至對文學文本評價的方向,甚至還會涉及到譯本是否與原文本思想內容一致的大問題。在莎士比亞研究中,選擇莎士比亞作品的何種文本和其他文學文本翻譯一樣,毫不例外應該受到應有的重視。對于中國出現的莎作譯本的原作版本進行梳理后,發現莎作的目前現有的幾個中譯本中,由于局限于譯者當年取得版本的條件,所獲得的原作版本不是很優,也不一種可能就是在當時翻譯時對版本問題重視程度不夠,“相當多的譯者忽視了莎作版本的選擇”[1],而導致譯本中出現了這樣或是那樣的問題。
辜正坤認為,目前莎士比亞的各種英文版本自莎士比亞第一個版本出現的四百年來,累積已經達到一千三百余種。而早年朱生豪與梁實秋譯本依照的是牛津版,這個版本在19世紀的莎學版本中,地位實在不能算是很高的。[1]方平的譯本主要“參照了歐美當代備受重視的Bevington全集本(1992年)與Riverside全集(1974年)”。[2]對于中國莎士比亞作品翻譯使用那種版本較優的問題,莎士比亞研究大家李偉民教授認為“最好采用J. D. Wisonde的新莎士比亞版。”但目前引進國內的版本中未見Wisonde的新莎士比亞版。不過令人欣喜的是,在一千三百種眾多的英文版本中,中國的莎士比亞研究專家已經為中國的莎學研究者與愛好者引進了《阿登版莎士比亞》。辜正坤對阿登版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首先從讀者角度,認為這個版本主要為學術界讀者和普通讀者(包括學者、大學生、演員、戲迷等)之用。對莎氏的每部作品都有一個長篇導讀兼序文,其主要目的是詳細介紹莎士比亞每一部作品的故事出處、劇本的基本結構、戲劇語言特色、人物的塑造、文體的風格、文本的沿革、時代背景、戲劇演出史及其他綜合性莎學名家的相關評論等。《阿登版莎士比亞》的特點是注釋比一般注釋本詳細,他認為這個版本對于中國外語界的文學研究者、翻譯者和英語學習者來說,無疑是當前最理想的版本。其次,在系列叢書中,有注釋方面歧義的情況下,把各家學說都呈現給讀者,當然校訂者同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是做主要是要達到評介客觀的目的,和中國古典學術著作《十三經注疏》或《周易折中》的做法有點相類似。此外,對四開本以及對開本到后世數十家重要校勘本中出現的異說,《阿登版莎士比亞》把他們如實的反映給讀者,這樣百家爭鳴的方式有利于文藝的進步,這也算是很大度的一種做法。在書的末尾部分有各類附錄,這些附錄往往與劇情原型相有關聯,或與作品的形成有較為明顯的淵源關系。而且書中的資料來源都有出處,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部分劇中還穿插有劇中格局樂譜,當時演劇的的基本構成情況等豐富內容。因而,阿登版可供閱讀欣賞,也可供研究之用,對于英語學習與研究大有幫助。[3]
除過新阿登版之外,似乎在國內引進原版書系列中再沒有象這樣的莎士比亞引進版行世。當然現在網絡發達,可以在各種網上購到國外的版本,但是買哪一個版本,沒有專家學者的指導還真是個問題。
對中國學者完成莎士比亞作品注釋的在中國也是寥寥無幾。目前有由裘可安主持,由國內莎學研究者分單行本進行注釋的一套莎劇自1984年陸續出版,到現在已經完成。但僅只這一套,遠遠不能滿足越來越多的莎學愛好者和學習者之用。而且這個版本現在多數已經脫銷,既然在網上也無法購得。另有羅益民2010年所著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名篇詳注》應該是第一本中國學者完成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注釋本,但不是莎士比亞全部154首十四行詩。除此之外,再沒有中國學者完成的莎劇與莎詩的注釋本,這在中國算是一件憾事!
那么在中國到底有多少莎士比亞的譯本,李偉民對其做了相關統計:不算沒有經過改譯、重校而冠以莎士比亞全集之名和重印出版的眾多版本,僅翻譯或經過改譯、增補、重校的《莎士比亞全集》就有6套,他們分別是朱生豪等譯(1978年人民文學版)、朱生豪、虞爾昌譯(1957年臺北世界書局版)、梁實秋譯(1967年臺灣遠東圖書公司版)、朱生豪等譯(1997新時代版)、朱生豪等譯(1998年譯林版)、方平主編主譯(2000年河北教育版)。[3] 另一莎學研究者辜正坤認為完整的中文版《莎士比亞全集》共有4種,分別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版,譯林出版社版,臺灣遠東圖書公司版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版。[4]辜正坤所提供的四種漢譯版本沒有給出具體的出版社與出版時間。但照上面李偉民所做的統計信息,辜正坤認為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是1978年版,譯林版當屬1998年版,臺灣遠東圖書公司版應該是1967年梁實秋版,而河北人民出版社這一版本應指方平主編主譯的《新莎士比亞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
從以上所提到的全譯本,去除以朱生豪為第一譯者的重復情況來看,實際在中國的全譯本僅只三套而已。對于以朱生豪為第一譯者的版本,只是補充了朱生豪所沒有完成的其余為數不多的幾個劇以及詩歌罷了。筆者認為真正意義上這不能計數為一個新的全譯本。
其他的所謂的全譯版本,只不過是重復翻印而已,雖然有些所謂的全譯新版認為對朱生豪譯本中出現的翻譯問題做了相關的修訂處理。
莎士比亞作品在中國駐足一百七十年之久,到目前為止僅只有三套真正意義上的全譯本,實為憾事。
當然,除過這三個全譯本外,對莎士比亞劇作部分翻譯的還有不少,如孫大雨的《莎士比亞四大喜劇》和《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卞之琳的《莎士比亞悲劇四種》和孫法理的《查理二世》等。
士比亞作品,除劇作外還有他的十四行詩。對于十四行詩的翻譯目前約有數十種之多。讀秀庫中以“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為搜索條件,可以找到97種出版書目(2000-2010(54),1990-1999(27),1980-1989(14),1950-1959(2))。主要譯者有梁實秋、梁宗岱、屠岸、曹明倫、辜正坤和艾梅等人。詩歌的翻譯最見譯者的文學功力,而且最不容易出現雷同或抄襲現象,以上六位名家相對于中國眾多學者而言,從譯者的數量上來看太少,即使有數十位也是不足以見出中國詩學的發達程度,因此還需要中國學者繼續努力,完成更多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翻譯工作。對于莎氏的長詩而言情況也是大致如此,需要更多的譯本出現。
如前所述,莎士比亞的全譯本僅只三套。即使這三套全本,從翻譯研究角度來看,“多年來莎士比亞翻譯研究并沒有引起莎學界的足夠重視,甚至也沒有引起翻譯界的重視,沒有或很少有人進行全面總結研究,已經出版的莎學著作和莎士比亞辭典對這方面也少有述及。”[1]
當前對于三套譯本的研究成果,目前多是字詞文字校對式的性質,不能深入到句法與篇章的層次進行,或是修辭文體方面的研究。這樣的研究方法是傳統方法。鑒于這種情況,莎學研究者還得利用新的研究手段,利用現在電子輔助工具完成相關研究。對于句法與篇章層面的研究可以借助于現在計算機工具開展基于語料庫的定量研究,以更為客觀的手段與方法探討莎士比亞的作品。
2結語
莎士比亞研究在中國正如翻譯研究在中國一樣還不夠發達。對于莎學研究者來說,首先要解決的是有更多的好的莎士比亞版本登陸中國,其次要有較好的文本注釋,這樣才能把翻譯工作做好。有了更多的譯本,中國的莎學研究才能更加的繁榮,這將進一步促進中國的文學發展及語言的豐富性。
參考文獻:
[1]李偉民.中國莎士比亞批評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285,273.
[2]胡開寶,鄒頌兵.莎士比亞戲劇英漢平行語料庫的創建與應用[J].上海:外語研究,2009(5):65.
莎士比亞的作品范文第3篇
莎士比亞戲劇的經典對話和場景,已經形成了思維定勢。如果說,這300多年里,我們讀的從來都不是真正的莎士比亞,你會作何感想?
莎士比亞最原始版本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所描繪的愛情悲劇并不像現在看到的那般精致、傷感。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朱麗葉在羅密歐死后給他深情一吻,其實是后來人為了渲染氣氛加上去的,莎士比亞最早并沒有寫過這個場景。
在莎士比亞的原稿里,《哈姆雷特》中的王子獨白部分沒有那么冗長;《奧賽羅》里也沒有奧賽羅在自殺前親吻妻子尸體的舞臺提示,甚至奧賽羅本人也沒有自殺;《李爾王》最早只是體現個人悲劇,而并非如今苦大仇深的王朝災難;《麥克白》中,麥克白夫人安撫丈夫,說他無需因為殺死英格蘭國王鄧肯而害怕,還保證他會安然逃脫懲罰。但是原始劇本中,麥克白夫人僅僅在詢問:“我們在害怕什么?”
后世對莎士比亞的作品有多種演繹,要命的是,戲劇作品中一個標點符號的變化,都可能導致人物性格及故事情節發生重大改變。據考證,沙翁的許多戲劇都有兩個版本,一個就是1623年出版的對開本,另一個是四開本,即那個時代流傳的盜版。莎翁撰寫這些戲劇后300多年間,編輯通常對兩個版本進行摘選和混合,最后形成新的版本出版發行。也就是說,在這300多年里,我們讀的從來都,不是真正的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其實也是那個時代的大眾文化偶像,雅俗共賞,遠不如現在被詮釋的那么高深莫測。
好的文學作品往往讓人看完之后心生感慨,有才之士大筆一揮添磚加瓦。英國利物浦大學的研究人員認為,讀莎士比亞可以使大腦活動更加積極。他們發現在讀莎士比亞作品中的某些文字時,大腦的反應與遇到某些難題時相似――如果答案顯而易見,那么人們很快就會因無聊而感到厭煩,但如果文字中表達的含義不那么簡單,大腦會表現得很興奮。莎士比亞喜歡在一些看上去很普通的句子中嵌入幾個生僻的詞匯,使閱讀者的大腦時刻保持高度警惕。
莎士比亞的作品范文第4篇
>> 利用《指南》提升家長科學育兒能力 用好《指南》 共筑育兒夢 “帶娃指南”透露的育兒信息,哪些可以借鑒? 傾聽莎士比亞 試論莎士比亞 掃描莎士比亞 發明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遠行 為了莎士比亞…… 走近莎士比亞 指南 猴子與機器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名言錄 梁實秋與《莎士比亞全集》 邂逅莎士比亞書店 湯顯祖和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神秘的背影 莎士比亞曾是個惡棍? 莎士比亞的恥辱穿越 莎士比亞在加拿大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中國 > 政治 > 莎士比亞育兒指南 莎士比亞育兒指南 雜志之家、寫作服務和雜志訂閱支持對公帳戶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周惠民")
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周惠民,臺灣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曾留歐十年
“哦買噶”莎士比亞系列是一次創新而大膽的嘗試,通過輕松活潑的呈現方式,讓年輕人更愿意接受莎翁的經典劇作。
愛情技巧? 沒問題。如何殺死國王?沒有人比他更擅長。讓莎士比亞提供育兒建議?還是省省吧,朱麗葉的父親幾年前就得去見社會服務部門的人,而哈姆雷特的媽媽早就得看心理醫生了,但是英國人埃姆斯?安德魯斯認為,莎翁還是有些東西教給爸爸媽媽們。埃姆斯?安德魯斯,曾任中學教師,現在住在英格蘭康沃爾郡,他圖文并茂的書《莎士比亞育兒指南》已經出版。
《莎士比亞育兒指南》每一頁都有精辟的評論和安德魯斯的幽默線條畫。讓我們來看一幅,“現在是詛咒你出生的時候了!”一位父親從床上坐起來,附身面對哭泣的孩子說,“我希望貪婪的狼吃掉你。”這些話引用自莎翁的《亨利六世》。
從寶寶出生的快樂到青少年后離家而去。從孩子出生后,大人的睡眠被剝奪到孩子挑食,喜歡可怕的音樂,這些問題莎士比亞都有答案,或者至少是有苦澀的詛咒。正如作者所言,孩子的工作就是激怒他們的父母,父母的工作就是被激怒,在這不幸的安排中蘊含著很多的幽默。
其實你可以隨時向莎翁學習,如果你的孩子在超市發脾氣,你就轉向其他購物者宣布,“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源于我,這種恥辱來自未知的恥辱自身”估計會有觀眾會知道這是引用在《無事生非》中的句子。當你的孩子快把你氣瘋了,你就告訴他,“求你讓我一個人呆一會兒,你去別的地方發泄你的愚蠢吧”。(《第十二夜》)
莎士比亞的劇作向來被視作英國文學寶庫中最耀眼的明珠,妙語連珠、扣人心弦,讓這些經典之作被莊重嚴肅的光環所圍繞。正統嚴謹的學者鐘愛紙上的優美語言,不喜枯燥文字的大眾亦可去劇院欣賞唯美的舞臺劇,不可撼動的經典一直在以各種傳統的形式為人們所品味。
然而古典風十足的著作未必是當下新新人類的菜,于是一些人腦洞大開,將莎翁名作進行改編,“哦買噶”莎士比亞系列(OMG Shakespeare series)驚艷亮相。其中網絡用語和表情符號的出現瞬間讓古樸的劇本充滿喜感,語言簡潔明快,風格嘻哈搞怪,迎合了年輕一族的閱讀習慣。
目前,已被“翻譯”為表情語言的莎翁著作包括《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雷特》、《麥克白》和《仲夏夜之夢》。讓我們來看看“YOLO朱麗葉”,這是蘭登書屋2015年推出的兩本莎士比亞戲劇之一。YOLO的意思是網絡用語“你只能活一次”。
“哦買噶”莎士比亞系列是一次創新而大膽的嘗試,通過輕松活潑的呈現方式,讓年輕人更愿意接受莎翁的經典劇作。該系列改編的最大亮點在于主角開始用智能手機聊天,頗具現代文化氣息,非常應景。這些書引發行之后,引起了渲染大波,一位教育專家,在《每日郵報》上,宣稱這些書“絕對是災難性的。” 認為這樣亂來會給經典帶來“毀滅性”打擊,降低了教育的含金量。
莎士比亞的作品范文第5篇
關鍵詞:莎士比亞 主題 創作意圖 英國文學傳統
伍爾夫一直被視為英國現代文學的先鋒,她的作品向來以新銳的寫作技巧、對人性的深刻洞見和極富詩意的語言見長。這部小說也不例外。《達洛維夫人》語言優美,以意識流的表現手法,在記憶與現實間來回跳躍,主要描繪了男女主人公各自在1926年6月的一天中的經歷。雖然小說采用了很多現代派的寫作技巧,卻同時引經據典,和過去的文學傳統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除了引用希臘神話和《神曲》中的典故,小說反復引援了英國文學大家莎士比亞的作品。莎翁的作品,在小說中不但被多個人物頻繁引用,其形象本身還作為一個文學意象,被作者賦予了多層含義。事實上,小說的構架就是緊緊圍繞著對莎翁劇作《辛白林》的影射構建的,而作者運用莎翁這一經典文學的代表形象有其文學上和非文學上的多重意圖。莎士比亞一直以來被奉為英國最偉大的作家,他不僅代表了英國文學的歷史與傳統,也是大不列顛帝國文化的結晶。正因如此,伍爾夫作品中對莎士比亞的引用并不能簡單地從文學意義上理解,而應把其放在更廣闊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中加以考察。本篇論文希望從《達洛維夫人》中對莎翁作品的引用入手,挖掘小說賦予莎士比亞這一文學形象的各種深意。本篇論文包括三部分,首先將探討莎翁的多部作品和小說的關系,及它們與小說的主題之一――死亡與復活的關聯,接著將論述小說中莎翁的形象是如何與作者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呈現和英國文化相聯系,最后將從女性主義視角探討莎士比亞這一形象是如何被作者運用于其女權主義事業。希望本文通過以上圍繞莎士比亞和作品關系的多層次探討,能幫助讀者加深理解伍爾夫的作品及其與英國文學傳統的深層聯系。
在去為宴會買花的途中,克拉麗莎?達洛維透過一家書店的櫥窗,第一次讀到了《辛白林》中的句子――“不要再怕炎炎驕陽,也不要害怕寒冬肆虐”。[1]9在原劇中,這句話出自女主人公伊莫金死后人們為她唱的挽歌,表達的是死亡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種解脫,將人們從生活的重負中解放出來。在小說中,對死亡的思考一直纏繞著克拉麗莎:“她的生命最終必定會完全停止,這重要嗎?沒有她而這一切必將繼續存在下去;她感到怨恨嗎?抑或,相信死亡使一切完全終結,不也令人感到安慰嗎?”[1]8當布魯頓夫人“只請理查德吃午飯而不請她”,而她知道“據說她的午宴非常有趣”時,克拉麗莎又一次深深感到時間、死亡的陰影在向她迫近――
但是她懼怕時間本身,并且,好像是刻在毫無感覺的石頭上的日冕,她從布魯頓夫人的臉上可以看到生命如何在衰退;她的那份生命如何年復一年地被片片切掉,剩下的空間里能夠伸展的余地是那么小,已不再像年輕時那樣能夠去吸收生存中的色彩、刺激與音調。[1]27
死亡的陰影一直圍繞在小說的主人公周圍,潛藏在看似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之下。這使小說對平常事件的敘述充滿著張力,甚至是緊張感和脅迫感。克拉麗莎反復吟誦莎翁劇中的那兩句話,想以此來對抗生命的消逝。這對她來說是一種安慰,象征著她“默認了死亡這一事實”,[2]90因為死亡就意味著“不再害怕”。
此外,《辛白林》中,伊莫金是假死,幾乎這部劇中所有那些被認為死去的人物,后來都被發現還活著。這一死亡到復活的循環貫穿整個劇本。同樣的,死亡復活的主題在《達洛維夫人》中也有突出表現。當達洛維夫人在宴會中突然聽到賽普帝莫斯死亡的消息時,她意識到“死亡是種挑戰。死亡是種傳遞思想的努力;人們感到無法達到那神秘地捉摸不到的中心……死亡中有著擁抱”。[1]164
對賽普帝莫斯來說,死亡是一種交流方式。在小說中,他將自己視作“復興社會的上帝……是替罪的羔羊,是永遠的受難者”。[3]23懷亞特曾指出:“替罪羊傳統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自殺承擔起所有的罪惡,從而使集體得到凈化和救贖;另一方面,其象征著必須被殺死的自然神,以保存其生命力到來年的春天。”[3]443因此,賽普帝莫斯的自殺實則是帶來了生命的可能,他為集體犧牲了自己的生命,而克拉麗莎也因他的死而獲得了對生命的嶄新認識,繼續鼓起勇氣面對生活。同時,也正因克拉麗莎懂得了賽普帝莫斯的所思所感,他的生命在她身上得到延續,他在另一種意義上獲得了永生,死亡和復活這一主題又一次得到了加強。此外,克拉麗莎在得知沒有收到布魯頓夫人午宴的邀請后,思索著“如能此時死去,此時將最為幸福”。這兩句話出自莎翁的名作《奧賽羅》,表達的是奧賽羅已經坦然接受死亡的心情,因為在原劇中,死亡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能讓愛永生。對于克拉麗莎,死亡是唯一能使她對莎莉的愛不受時間侵蝕的東西。后來,在聽到賽普帝莫斯死去的消息后,克拉麗莎反復在心中默念這兩句話,她體驗到賽普帝莫斯的思想和感情,在這一刻兩個人的生命產生交集,兩人同時對死亡有了嶄新的認識――死亡并不可怕,應該平靜地去接受它。所以,克拉麗莎為他感到高興――“她很高興他這樣做了;拋棄了一切”,[1]167而其他人還得繼續生活下去。最后,克拉麗莎帶著這份新的認識,重新鼓起勇氣回到了自己的宴會中。
小說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給英國帶來了沉重的傷痛――“這個世界的最新經歷使他們所有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心中溢滿淚水”。[1]9這一背景使上文中提到的《辛白林》中的那兩句話更顯重要,因為此時對死亡的恐懼變成了一個群體感受,而克拉麗莎反復吟誦它們不僅僅是在給自己心理安慰,也同時是給那些飽受戰爭折磨的人們以安慰。對于賽普帝莫斯來說,“他去法國,為了拯救一個幾乎完全由莎士比亞的劇作和穿著綠色裙衣在一個廣場上散步的伊莎貝爾?波爾構成的英國”。[1]76然而,一戰使他徹底地對這些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在戰前,莎士比亞對他來說,象征著大英帝國的歷史與文化還有他所有對美好的幻想,在戰后卻僅僅是“語言的優美”。
少年時對語言的陶醉之情――《安東尼和克利奧佩特拉》――已蕩然無存。莎士比亞是多么厭惡人類啊――穿衣服,生兒育女,口腹之骯臟![1]79
賽普帝莫斯對莎士比亞興趣的減退,從一個側面表現了戰爭對人性的摧殘。原本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他,現在卻開始對一切都不信任――“因為事實是,人類既無善心,又無信念,也無寬容,有的只是能增加眼前快樂的東西。”[1]80
另外,莎士比亞在小說中的作用還可以從英國文化這一角度入手考察。
克拉麗莎將莎士比亞和其童年的經歷緊密聯系起來,她故鄉新鮮的空氣、海浪、花草樹木,這一幅極富英國特色的圖景讓人容易聯想到英國文化。這正是伍爾夫在批評所謂的愛國主義,但是她珍視人對土地的情感和對過去經歷的留念。[2]92
通過反復吟誦莎翁作品中的句子,克拉麗莎實則是在向英國過去的文學傳統致敬,而這一傳統正是代表著英國文化的延續性和歷久彌新的生命力。伍爾夫還用布魯頓夫人這一形象和克拉麗莎作對比,前者聲稱自己從來不讀莎士比亞,因此她在書中的形象也被刻畫得嚴肅冷漠。不同角色對莎士比亞的態度有著鮮明對比――克拉麗莎和賽普帝莫斯對其的喜愛,以及理查德和布魯頓夫人對其的毫不在意。理查德聲稱“正經人都不該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1]67并將讀他的詩比作“湊在鎖眼上偷聽”。作品中的布魯頓夫人也不讀莎士比亞。在小說中,閱讀莎士比亞代表著一個人對情感和美好的追求,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角色身上這些特質的缺失――理查德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對克拉麗莎的情感,而布魯頓夫人更是被看做更關心政治而不是人。
無疑,莎士比亞對英國人來說是經典文學的象征。伍爾夫通過在作品中多次引用莎翁的作品,實際上是想“將文學從受教育的人手中,從等級制中,從軍國主義和自我中心者的手中解放出來”。[2]92
伍爾夫從容地引經據典,并非是想用過去的文學經典為自己的文本服務,而是希望將它們融合到自己的聲音中來,讓兩種聲音合而為一。[2]93
伍爾夫對莎翁作品的引用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借鑒,其背后潛藏著她關乎女權主義目的。一位學者論述道:“莎士比亞對于伍爾夫來說,不是一個父親式的形象,而是一個母親式的繆斯,給她帶來靈感,提供榜樣,幫助她構想出女權主義的前景和實現方法。”[4]722“并且,通過轉變人們對莎翁形象的預設,伍爾夫是在向人們普遍認為繆斯―詩人之間應該有的性別關系提出挑戰,從而瓦解傳統的性別預設。”[4]742因此,《達洛維夫人》中對莎士比亞的影射也可被視作伍爾夫挑戰性別偏見的一個手段。對她來說,莎士比亞的思維是“雌雄同體的,既是男又是女的”。[5]102同樣的,作品中,莎莉和克拉麗莎都被描繪成雌雄同體的形象。莎莉年輕的時候就一直以叛逆著稱,不接受社會對傳統女性角色的設定,而克拉麗莎在小說中一直有個“男性”的她――賽普帝莫斯。通過賦予莎翁形象以新的含義,伍爾夫是想告訴讀者們“女性的讀者和作家也可以成為文學的中流砥柱”。[2]231
綜上所述,莎士比亞對于伍爾夫來說,不僅是一份可以從中獲取各種靈感的文學寶藏,也是一個象征著英國性、經典傳統和父權制的文學偶像。正因如此,《達洛維夫人》中的莎士比亞形象是復雜的,擁有多層內涵的,與作者的寫作意圖密切相關。通過探討莎翁形象和這部小說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到,伍爾夫作為一個現代派的小說家對傳統的繼承和反叛。
參考文獻
[1] 弗吉尼亞?伍爾夫.達洛維夫人[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2] Jane de Gay.Virginia Woolf’s Novels and the Literary Past[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
[3] Wyatt,Jean M.Mrs. Dalloway:Literary Allusions as Structural Metaphor[J].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Vol.88,No.3(May,1973):440-151.
[4] Schwartz,Beth C.Thinking Back Through our Mothers:Virginia Woolf Reads Shakespeare[J].English Literary History,Vol.58,No.3(Autumn,1991):721-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