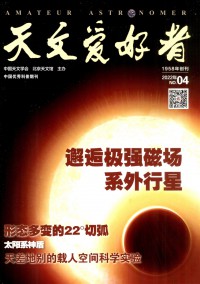天文學基礎知識入門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天文學基礎知識入門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天文學基礎知識入門范文第1篇
占星術起源于4000多年前古巴比倫王朝時期,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牧羊人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為了畜牧、農耕的方便,研究總結出天空星辰和季節變化的關系。為了讓這些知識利于流傳后世,人們將雜亂無章的星空想象成不同的形象,并為之取名,這便是最初的星座由來。
星座在古巴比倫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古巴比倫人對占卜篤信不移,大到國家征戰,小到商店開張,都要卜問吉兇,占星術則是最常見的占卜方法之一。人們認為地面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天穹的映射,日月星辰的運行預兆著國家和個人命運,天氣的陰晴冷暖也意味著人間事務順利與否―如果7月的第一天是陰天,就必然發生戰爭;如果第13天和第19天也是陰天,那么國王有性命之虞。在他們看來,占星術和羊肝占卜法一樣準確無誤―羊肝上的形狀和花紋是神靈留下的記號,而神不僅會帶來食物,還會通過自然現象暗示未來。
第一本分門別類論述天體預兆學說的著作出現在公元前18世紀到公元前16世紀,用楔形文字寫成。直到1000多年后,占星術才逐漸傳入埃及、希臘等近東地區,再由印度僧人傳到中亞。公元7世紀,占星術被傳入中國,但認可程度從未超越本土文化孕育的周易學說。
在漫長的發展中,占星學以目的劃分,形成了四大流派:本命占星學,也就是最為流行的根據個人命盤來推斷性格特點和一生運勢;時事占星學,比如政治占星學、財經占星學、國際局勢占星學、氣候占星學等;卜卦占星學,就某一具體事件就事問事;擇日占星學,選擇好日子、好時辰來開展某項工作。
在這四大流派之外,按照方法論來劃分,占星術門派眾多。西洋現代占星學講究大量運用心理學知識,是目前港臺占星界的主流,它的前身是傳統占星學和古代占星學。按照地理范圍來分,有漢堡占星學、印度占星學、阿拉伯占星學等,在東方占星體系中,比較有名的包括使用二十八星宿的宿曜派和運用天干地支的七政四余派。不過,埃及、希臘、羅馬、伊斯蘭流派均已中斷,只有西洋流派和印度流派尚有傳承。 專業學科有“占星學院”不代表承認占星學科學 美國讓“占星學院”通過資格鑒定并不表示承認“占星術”,只是承認該校有能力讓學生學到它所承諾的東西。
17世紀后,隨著日心說的確立和近代科學的發展,星相學失去了科學根據,占星術也被視為古代迷信的一部分,逐漸失去了和天文學同等的位置,但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占星術仍然被當成一項學科研究,在大學占據一席之地。
2007年,印度大學撥款委員會在全國20所大學設立“吠陀占星術”專業,并向開設了這一專業的大學提供2000萬盧比(約合43萬美元)的研究資金。印度大學的研究資金向來吃緊,這一刺激政策引來了至少45所大學的激烈競爭。
吠陀占星術指的是公元前13世紀前后在印度形成的古代占星術。這是獨立于西洋占星學體系的另一個系統,不涉及對性格和心理的探討,著重研究出生時就注定的一生命運。
撥款委員會認為,研究占星術能“幫助研究印度教在數學、氣象學、農業科學和空間科學上的成就,還能使人們以時間為尺度了解人類生命和宇宙空間里發生的一切”。
這一政策受到數百萬印度占星術從業者的歡迎,不過社會反響并不理想,不僅引發民眾質疑,也引起一場席卷印度教育界和學術界的大討論。印度媒體爆料稱,印度“教育部”力捧占星術,只是因為上級部門負責人是占星術的忠實信徒。
在美國教育系統中,也可以看到占星術的身影。2000年,開普勒學院開設占星學方向課程,四年后,八名畢業生獲得占星學研究文學學士學位,在西雅圖音樂博物館舉行了畢業典禮。不過,幾年后,開普勒學院便關門大吉。
在開普勒學院開設占星方向課程的后一年,美國亞利桑那州“占星學院”通過聯邦政府“職業學校暨技術學院資格評鑒委員會”的鑒定,成為全美國第一個獲得政府立案承認的“占星高等學府”。獲得政府認證后,該學員便可以促請聯邦教育部批準其學生取得聯邦補助的經費與貸款。 占星術在阿拉伯世界也有很深遠的影響,2006年多哈亞運會,星盤就被卡塔爾人變成了開幕式中的重要道具。
對此,華盛頓“高等教育資格鑒定委員會”主席伊頓女士表示,讓“占星學院”通過資格鑒定并不表示承認“占星術”,而只是承認該校有能力讓學生學到它所承諾的東西。紐約“海頓天文館”的天體物理學家泰森表示,現代科學于600多年前萌芽時,人們就發現“占星術”不足信,在21世紀的今天,還有學校開班教授占星術,令人不可思議。
但是,占星術的擁護者們仍然認為這門技術在現代社會不僅相當必要,而且從業者收入可觀。金融占星師被認為是這個群體中收入最高的一部分。他們通過每日星空變化預測金融市場走向,從而讓投資者進退有度。
據說金融大鱷索羅斯的智囊團中有兩位占星師,而高盛集團曾在1999年表示日月蝕和日本股市以及美國國債收益率存在聯系。但這些傳聞從未被證實過。 職業資格認證難度不亞于司法考試
中國國內沒有正規占星師培訓機構,更沒有占星專業,但卻并不缺乏各種名目的占星師。在各路占星師當中,擁有“倫敦占星學院”畢業證的占星師最受信任。這家全球最為著名的占星師培訓機構在外人看來就像哈利?波特的魔法學院,它的中國畢業生“星座小王子”目前已是香港最炙手可熱的占星師之一。
倫敦占星學院成立于2000年,創立者是兩位占星師,其中一位的著作《當代占星師手冊》已經出版中文版本,是國內占星師的必備圣經。進入這所占星學院并無門檻,無需通過入學考試,但要拿到畢業證并不容易。
對零起點的初學者來說,第一學期的培訓每周進行一次,一共八次。學生會在具有職業資格的專業占星師指導下學習行星、元素、標志等基礎知識。
在第二學期的學習中,學生不僅要掌握十二星座的角度、星宮、規則、縱橫模式、圖表選型、太陽月亮周期等基本天文知識,還要學習如何向客戶解釋星座和他們命運的關系。
在兩個學期的學習之后,學員就算是入門了。不過想要獲得學位,還需要念完第三學期,并通過占星考試。
天文學基礎知識入門范文第2篇
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整體格局的調整,文學和文學專業在高等學校、學生心中的位置也有所“調整”,按照溫儒敏的話,“考上中文系的學生大多數不再是第一志愿(綜合性大學普遍如此,師范院校情況稍有不同),學生都很實際,不太愿意學中文;而且受應試教育的約束,中學階段接觸作品不多,甚至語文都還沒有完全過關,上現代文學又沒有相關學科的學習作基礎,學起來的確比較困難。”[1]面對文學在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心中位置已經“下降”的狀況,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怎樣調整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現當代文學對話式教學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結合的重要性
作為高校漢語言專業主干課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基礎課程,也是剛剛完成高中階段教育的大學新生在中文系文學類的入門課程,因此對現當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效果、教學理念的重視和更新直接關系著大一學生對于文學的興趣、文學文本的解讀、文學史和文學理論掌握等能力的培養。對于大學新生來說,現當代文學的地位可謂在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課程中兼有興趣引導員、學科領路人和文學能力普及者的角色。特別是對于一些地方高校,近年來有相當數量的入學學生已非第一志愿報考中文專業,甚至有部分學生在高中階段為理科學生,他們對于文學文本的閱讀、文學史的掌握、文藝基礎知識、文本理解能力等本來就很薄弱,這為地方高校的中文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和模式提出了嚴肅的課題,而作為中文系大一學生專業必修課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肩負著使這一類學生完成角色轉變、知識結構轉變、實現中文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重任。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對話式教學即被教育人士提出和重視,今天已經成為大部分課程教學的重要理念之一,它使課堂中的教師與學生地位平等,變以前滿堂灌“獨白”與填鴨式的教學形式為互動、交流、交往式的教學。但這里存在一個問題,對話式教學需要對話雙方對話題有深入的體驗和認識,特別是需要對話雙方對同一話題在對話進中有火花般的碰撞,繼而對參與對話者觀點、思想有所影響和改變。在實際課堂中,許多對話式教學卻僅流于形式,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學生對教師提出的話題缺乏必要認識,所以無奈之中對話式的教學就又變成教師的“獨語”或只有少數學生與教師開展的對本文由收集整理話。“先有‘間性’,而后才有‘交往’,因為‘交往’就是至少兩種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互往來。‘有來有往’才能謂之‘交往’,這意味著,失去了反饋聯系的交往系統并不存在,而交往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溝通。”[2]可見,僅僅有對話的姿態和形式是遠遠不夠的,它還需要學生的密切配合,而配合的關鍵即在于學生素質的整體、全面的提高(孤獨的個體的提高對于對話式的課堂教學是遠遠不夠的,這會造成教師只與個別學生有良性的對話,而其他人徹底“淪為看客”),加之專業學時的整體性壓縮,所以學生自主性的學習成為對話式教學得以良性互動并取得效果的關鍵。
此外,僅僅靠學生獨自摸索的自主性的學習是不夠的。自主性學習需要在專業架構之下完成,需要在成熟的、合理的指引下確立學習目標、補充學習動力、完善學習方法、調整知識結構。可以說僅僅有自主的姿態是不夠的,僅僅賦予學生自主的權利也是不行的,因為依賴學生素質的自主性學習如果缺乏指引和規范就會淪為無“主”可“自”、“六神無主”的學習。“除非對話雙方進行批判性思維,否則真正的對話也無從談起。”[3]在實際的教學之中,往往教師與學生一對一的教學方式,甚至小班教學都因為種種原因難以為繼,所以非常有必要在課堂有限時間里,以課堂教學形式來規范和強化學生的自主性學習,在課堂的對話性結構里來學生的自主性學習確立起來,完善展開。
二、對話—自主學習能力培養的教學實施措施
(一)按照學生層次有針對性地實施對話—自主學習能力培養的教學
學生學習興趣、能力、態度不盡相同,與其讓所有學生在一堂課上“一勺燴”,不如分層次教學的效果來得好,而這種層次的劃分無論通過考試、憑借志愿報名等形式都無法做到絕對準確和科學,所以怎樣劃分出層次是重點與難點。因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習時間比較長,因此,教師可以在新生入學第一個月的教學之中,對授課的對象予以考察,并通過提問、填報志愿、興趣、及作業的完成效果等來確定其屬于哪一個小組。因為學生精力、課時安排等問題,可將一個自然班級編制的學生可以分為兩個大組:研究組與基礎組。研究組由顯示出濃厚的現當代文學學習興趣、水平大體相當且有一定的文學鑒賞基礎和能力的學生組成,基礎組則由余下學生組成。基礎組以一般文學常識的傳授和文學基本鑒賞能力的培養為主,教師根據成員的自主學習能力的共性問題調整講授思路,調整教學方法,對文本的深度問題上根據學生實際情況進行調整;研究組則重在對小組成員文本解讀與研究能力的提升,略去基礎型、常識性知識的介紹。如面對傷痕—反思文學的內容時,基礎組可以以討論有代表性文本為主;研究組則在重點文本解讀的基礎之上,可以在深度、廣度上進行拓展,如將傷痕—反思文學與十七年文學進行比較,或從當時引起爭議較大的傷痕—反思文本來看待八十年代文學對既有文學規范的延續和調整等等。
(二)在對話中針對學生個體差異滲透自主學習能力培養
無論是研究組還是基礎組,教師都需要根據兩組學生個體成員的實際興趣、關注程度來調整對話教學內容,并在與學生對話中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態。“自主學習是指學習者根據自己具體情況通過確立學習目標,制定學習計劃,選擇學習方式,監控學習過程及自我評估學習效果等方式進行自我管理。”[4]學生自主學習的自覺和能力是不能依靠教師單純的“教”和“布置”就能得以完成,而需要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之下主動地發現文學的“妙味”、“趣味”,并在這種體味中探求適合自己的專業學習方法。教師在學生自主探索中并不是袖手旁觀的,而是要利用每一節課與學生對話的機會來對學生的學習能力和方法進行評估,并在恰當評估的基礎之上因材施教,加以適時、適當引導,直至他們每一個人都探索到適合自己的學習路徑和學習方法。
轉貼于
(三)立足課程特點,在與前沿研究成果和當下文學現象對話中建構能力
作為一門年輕學科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毋庸置疑的是它是一門行進中、不斷延伸至當下的課程,可以說今天的文學實踐就可能是明天文學史的一部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這樣的特點既給它帶來了一定的不穩定性,因此它的經典作家作品時過境遷后經常引起爭議紛紛;另一方面也因為這種不穩定性使它具有一種別樣的活力和動感。中國現當代文學課堂上,教師可以積極吸收最新的、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即使富有爭議亦可引入教學之中,這樣顯然能拓寬教師教學思路與學生視界,使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活力與動感的特點在課堂中彰顯;同時,這樣的方式又能夠將本學科的知識延伸至文學理論、古代文學、語言學、人類學等領域。此外,中國現當代文學又是不斷面對當下的文學現狀的,因此本課程不應該是一門封閉的課程,它更應該帶領學生直面當下文學熱點,通過師生與當下文學現象的對話、爭鳴,使學生作為一個親歷者、文學批評者真正參與到課堂教學的實踐之中、參與到文學現場里,那么這樣獲得的收獲是空前的。
(四)以多種對話形式提升學生學習動力
真正的對話就是“讓學生自己去‘聽’,讓學生自己來‘說’,再加上教師是對話者之一而‘不應以教師的分析來代替學生的閱讀實踐’”,“這體現了教學對話理論、閱讀對話理論的精神”。[5]這種理想的對話氛圍的創設需要適當改革傳統的文學類課程授課模式。傳統的文學授課模式是“教師臺上本文由收集整理站,口若懸河;學生記筆記,頭昏腦脹”,由于許多高校中授課班級班額較大,教師無法也無條件與學生進行一對一的溝通和交流。在目前無法該變的狀況下,教師可以根據教學進度來安排具體課程的形式和教授方式,化整為零,采用多種形式力圖與學生個體產生對話,在這種對話之中使學生的學習動力自主地加以提升。教師可以建設課程學習bbs,利用課下業余時間對學生提出的問題進行答疑,對其中有共性的問題亦可在課堂上集中講解。教師還可以利用博客、微博等來與學生進行互動,這樣將一個更加豐富、多元、多層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呈現給學生。在課堂教學之中,對話式的教學也不應拘泥于狹義的對話的形式——學生提問,教師來答的形式,可以以多種形式促成師生思想的交流,如小組討論式的教學、根據課程內容適當應用多媒體、原著與改編的影視作品對比分析討論、方言讀詩會等,力圖立足嚴肅教育的基礎之上,以一個輕松性的教學環境創設來使學生達到能力的提升。
(五)考核方式的調整與匹配
對話式教學形式是與考核方式的調整息息相關的,傳統的文學課程考試在本質主義的思路之下側重知識點的考核,學生文本解讀的個性化在“普遍性”的名義下予以武斷地“排除”,因此考試對于學生而言成了死記硬背才能應對的、談不上興趣的所在。同時這樣的考試方式也反身成為了枷鎖,牢牢地桎梏在教師頭上,扼殺了他們對內容的解讀和發揮。由此可見,教師欲創設與學生對話的課程語境,欲培養并激發學生對于現當代文學的自主性學習能力必須也要對課程考核方式進行調整,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相配套。可見,只有考核方式根本改革之后,學生才徹底擺脫“存儲”式的u盤人,真正成為一個主動攝取知識、主動思考的主體,與此同時,教師也不再是一個“照本宣科”的“復讀機”。考核方式的調整可以在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從考核內容入手,二是從考核形式入手,而這種考核內容與考核方式的調整也可按照對話教學的分組來分層次考核。從考核內容的調整來說,考核的內容應該以考察學生文本分析、解讀的能力為主,學生的分析和解讀只要立足文本、論據較為充分、文章精彩即符合考核要求,那些死記硬背的文學常識可以滲透到考核內容里。考核形式應允許多種靈活的考核形式,不再單一地用一張試卷來決定學生對這門課的掌握程度,可以在一個學期中,多維度地衡量學生對于現當代文學的理解,如學生可通過提交文學批評文章、與教師交流閱讀心得或文藝現象看法等,老師以此作為考核的指標之一,而不再依賴一張考卷;教師也可以適當利用互聯網,讓學生課后提交論文,只要保證文章原創性即可,不需組織統一考核;還可以在基礎組中允許學生通過多種形式表達對于作品的理解,如排演、拍攝自己改編的現當代文學作品等。
韋勒克和沃倫在談到文學的評價的問題上認為:“藝術作品的成熟指的是它的包容性,它的明晰的復雜性,它的冷嘲和緊張性等;小說與經驗之間的對應和符合關系決不能用任何簡單的逐項相應配對的方法來衡量,我們所能采用的合理方法是以狄更斯、卡夫卡、巴爾占課或托爾斯泰的整個世界來同我們的整個經驗即同我們自己想到和感覺到的‘世界’來作比較”。[6]既然文學與經驗、與世界比較而言,它們同是一個復雜的“世界”,那么用單調的、程式化的、忽略個性和創造力的考核方式來衡量學生對于課程的理解,顯然是極其缺乏合理性,這也不符合現當代文學學科要求。
三、需注意的問題
(一)對話教學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應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
對于解讀者來說,文學是重要的實踐行動,而以解讀文本、提升解讀能力為目標的現當代文學課程更是一種實踐。對于文學入門者和門外漢的大一學生來說,他們還有待確立有深度的文學觀念、文學理想、文學思維方式,因此,教師的主導位置是毋庸置疑的。在現當代文學課堂中,學生與教師的對話中所獲得的收獲要遠遠勝過學生內部的交流,所以,在課堂上,教師要特別重視與學生的基于文本解讀的對話,只有在這種對話中才能了解學生的能力、學習目標和學習方法的問題,才能夠對其自主學習能力的誤差給予有效指導。雖然教師在對話式教學中是起主導作用的,但自主學習能力的擁有者、主體是學生,所有的對話都旨在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因此必須尊重、保證學生在對話式教學中的主置。如面對學生普遍關心、引起頗多爭議的郭敬明抄襲事件、“韓白之爭”、梨花體、羊羔體、韓寒被疑抄襲等文學熱點事件時,可以在不預設答案、自由討論的前提下,讓學生自由抒發觀點,并有意識地引入文學史上相似的事件進行對比,以不同的理論視角和史實對這些事件進行解讀,培養學生自發地搜集、研讀史料和應用文學理論知識的能力,從而真正達到對話與自主學習相得益彰的效果。轉貼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