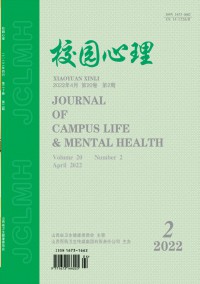心理學的鏡子療法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心理學的鏡子療法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心理學的鏡子療法范文第1篇
教師在指導學生調適不良情緒時,可采用以下方法:
一、遺忘調控
有的學生在消極情緒產生后,老是郁積于心,耿耿于懷,放不開,丟不下。結果,只能使這種消極情感不斷蔓延且日益加重。因此,當某種事情引起你的消極情感時,最好能把這件事盡快地遺忘掉,不要老去想這件事。因為你為這件事去悲傷、難過、嘆息,已經無助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增加你思想的負擔,使你的身心受到壓抑。應當明智一點,現實一點,事情既已發(fā)生,且無可挽回,就應當果斷地丟開它,忘卻它。如果這個場所老是引起你不愉快的回想,那就應當設法避開這個場所,以免“觸景生情”,如果眼前存在著一件可以喚起悲傷記憶的物件,不妨把這個“紀念品”收藏起來,以免“觸目驚心”,如此等等。這樣,就能使自己的思想暫時地離開這些不愉快的事情,以求得對它的淡漠與遺忘,從而緩解消極情緒對自己的侵擾,避免由此所造成的身心損傷。
二、轉移調控
現代情感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在發(fā)生情緒反應時,人們頭腦中往往有一個較強的興奮灶,此時如果另外建立一個或幾個新的興奮灶,便可以抵消或沖淡原來的優(yōu)勢興奮灶。因此,當情緒激動起來時,為了使它不至于立即爆發(fā),使自己有冷靜分析和考慮問題的足夠時間和機會,可以有意識地通過轉移話題或做點別的事情的方法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也可以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如咬住舌頭強迫自己不講話,數數等來緩解自己的情緒緊張。在余怒未息時,可以用看電影、下棋、打球等正當而有意義的活動,使緊張的情緒松弛下來。
三、宣泄調控
情緒宣泄有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直接宣泄即直接針對引緒的刺激來表達情緒。當直接宣泄于己于人都不利時,可用間接宣泄使情緒得到出路。正因為這樣,當學生心中有了不平之事并引起情緒激動時,可以向老師匯報,或向周圍的同學、親友等傾訴,并接受他們的勸慰和批評、幫助。這樣,通過情緒的充分表露和從外界得到的反饋信息,可以調整引起消極情緒的認知過程和改變不合理的觀念,從而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同樣,當與同學鬧了矛盾時,要勇敢地與對方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以解開疙瘩,消除誤會。萬不得已,在好朋友面前大哭一場,訴說心中的委屈與痛苦,心理壓力也會減輕一些。
四、升華調控
升華是改變不為社會所接受的動機、欲望而使之符合社會規(guī)范和時代要求,它是對消極情緒的一種較高水平的宣泄,是將情緒激起的能量引導到對人、對已、對社會都有利的方向去。當人遇到不公平之事時,一味生氣、憋氣,或頹唐絕望,都是無濟于事的;作出違反法律的報復行為更是下策,因為這是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正確的態(tài)度是有志氣,爭口氣,將挫折變?yōu)閯恿Γ錾钪械膹娬摺K^“化悲痛為力量”就是這個意思。
五、音樂調控
情感心理學家通過研究證實,音樂能通過物理和心理的兩條途徑對人發(fā)生影響。音樂的物理作用是通過音響來影響人體的生理功能。音樂通過人的聽覺器官和聽神經傳入人體中,和機體的某些組織結構發(fā)生共鳴作用。美妙的音樂通過被人體吸收,使人體的能量被激發(fā)起來,從靜態(tài)變?yōu)閯討B(tài)。音樂的心理作用在于,優(yōu)美的音樂能促使人體分泌一些有益于健康的激素、酶和乙酰膽堿等物質,起到調節(jié)血液流量和神經細胞興奮的作用,另外,音樂對邊緣系統(tǒng)、腦干網狀組織等同情緒的神經機構能發(fā)生直接作用。由于每首樂曲的節(jié)奏、速度、音調等都不盡相同。從而可以表現出不同的情緒調控效果。
六、合理情緒療法
心理學的鏡子療法范文第2篇
正如我的朋友季國清先生所說,物國(此為作者虛構――編者注)的社會結構,同時也是人存在于世的款式,在某些層面,就是停車場上把汽車重疊在一起的樣子,停放的車不是一輛一輛地單獨平擱,而是一輛一輛上下碼在一起。可想而知,處在這種層面結構中的人,要么被別人壓榨,要么去壓榨別人;要么被別人盤剝,要么去盤剝別人;要么被別人拖累,要么去拖累別人。相互牽制,動彈不得。實際上,這種壓榨、盤剝、拖累的結果,就是病。很多人不知道,我們的很多病其實就是這么得的,這么來的。
有一次在新春聚會上給一個大學教授敬酒,我對他說:“我們可以不聽專家的話,甚至不聽‘道德’的話,但一定要聽身體的話!”
我想強調的是:自身(身體)是不會錯,不會病的,錯的、病的總是自我,是自我讓自身出了錯,犯了病。在此我們碰到了漢語語用上經常會出現的麻煩,漢語的“自我”與“自身”是容易混淆,不易區(qū)分的,但我還是想特別加以說明:“自我”指的是“我”的思想、觀念、意識、想法、精神的形態(tài)與內在的狀況,而“自身”指的是“我”的身體,是造化、自然賦予“我”的一個肉身文本,且該文本皆具一種上帝恩賜的正常格式。如果人的意識在其上書寫正常的內容,身體就會正常。否則,就是不正常。輕度的不正常叫偏差,嚴重的不正常,就是病。但奇怪的是,明明是我們的意識、思想、觀念、精神讓我們的身體生了病,我們不但不去意識、思想、觀念、精神的層面尋找原因,反而一味地對著身體醫(yī)病。不但不去走自然療法、順勢療法、話語療法、暗示療法、心理療法的主路,反而只知道求助醫(yī)院、醫(yī)生、藥物、手術的輔道。這情形就好比,汽車的指示燈亮了,我們不去查看水箱、油箱,不去檢查發(fā)動機、油路、電路、剎車裝置,而是去拆卸指示燈,檢修儀表盤;煙霧報警器響了,我們不去尋找火源,而是去關掉報警器。我們皆生于無知,死于無知,當然,也更是病于無知。無知是由于我們的腦袋被上了夾板,意識被嚴重遮蔽眼睛沒有完全打開,盯芝麻,不看西瓜,或者把芝麻當成西瓜,只想坑洼,不思星辰;或者腦袋被擰成了麻花,一改變,就碎成齏粉。無知是由于我們截斷了污泥與彩云的連接,要么全是污泥般的顢頇、粗俗、卑鄙、匪氣,要么全是彩云般的虛幻、蒼白、貧血,不能讓污泥與彩云通過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心靈連接起來,貫通起來,形成一個無法分割的整體,使我們在污泥時,夢想彩云的天空;在彩云時,不忘腳跟的污泥。實際上,所謂比較健康的人,就是總是能讓污泥與彩云連線的人,總是能把污泥與彩云的比例弄得恰到好處的人。 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這是一種機械思維
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從頭到腳,從腳到頭,只知道在身體上下苦力,使蠻勁,打轉轉,這是物國文化、物國人民的悲哀。追根溯源,這是科學主義、無神論思想埋下的禍根,是一種邏輯的必然,當然要結出自作自受的苦果。
實際上,治病醫(yī)病的康莊大道是存在的,就在那兒擺著。只要逾越固定的偏見,沖破習慣性思維的圍堵,它就會給我們提供無數的或然與可能,展示一個巨大的空間。只是人們睜眼不見,充耳不聞,棄而不用。我認為,治愈的正道是:從靈魂精神身體醫(yī)院醫(yī)生藥物,而不是相反:從藥物醫(yī)生醫(yī)院身體精神靈魂。
身體不會病,是自我讓其病。更準確地說,是我的意識、我的思想讓身體病。所以,任何身體的保險,如果沒有保上精神險,都是白搭,等于是做無用功。也就是說,身體險的有效性是以精神險的參保與否為其前提條件的。沒有精神險的身體險毫無意義,因為疾病就其本質來說,是意識的內容,精神的故事,靈魂的事件。健康是個雙保險概念,身體險加精神險。尤以精神險為重,因為不病或治病的真正良方歸根結底并不是通常理解的手術、藥物,而是盡量寬廣的意念,盡量澄明的思想,盡量順應自然的道路,契合天地的節(jié)律。
前不久,我還對一位患病的朋友講過:實際上,一切的藥物、手術、醫(yī)院治療都是輔助手段,主要的途徑應該是意識的梳理、思想的澄明和觀念的校正。也就是說,治愈是意識中的事情,它永遠是一則心靈的故事,是一樁靈魂的事件,是對生活本身的確診尋藥,救助治愈。
我認為,生病并不可怕,因為在我們這個焦慮的時代,中這種負彩票的機率太高。但只要我們自己能成為我們自身一切事務(包括我們患病的特殊時期)的主宰,不把自己的命運完全交付給我們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不把我們的責任全部推諉給我們自身之外的所謂客觀的原因,疾病就會成為一樁我們自己可以承接、應對、處理的事務。實際上,只要我們沒有被污染、誤導得太過嚴重,我們自己都能理清楚,我們的病究竟是怎么來的,對我們的病就有某種內在可梳理的預感。同時,對化解疾病的路數大體上也會有一個輪廓清晰的預案。不過悲劇的是,我們早已喪失了這種預感、預知能力。我們對自己的疾病多半已沒有任何自我可以把控的自主性可言。
物國人似乎先天就處在一個易患病、而又不易病愈的境地,因為我們先天就缺乏必要的思想資源和靈性資源。我們先天就缺乏很多很多的東西,后天又在不斷地剔除很多東西。缺乏和剔除的,全都是保證我們的生命正常和健康所必需的。兩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我們就成了唯身體但又不能理解、不會善待身體的身體主義者。道理很簡單,一個精神進化不充分、不徹底,意識凋敝、觀念荒蕪、思想閉鎖、視界縮窄的人,是無法通過精神的檢索、思想的探源、觀念的辨析來療病扶傷、治病救人的。因為我們缺乏思想的資源,不知諸觀念的關聯,更不明白意識之無意識化的調控機理。無思想積累和精神資源的個人,肯定無從談起個人的成熟,個人的獨立,更無從談起個人的責任。也就是說,這樣的背景只能產生歪歪倒倒、不能用自己的雙腳來站立的人,只能產生無數不能自控,不能自主的家伙。結果,一生病,心頭就沒有底,沒有譜,只能把本該由自己來擔當的一切毫無保留地拱手交給別人,交給醫(yī)院、醫(yī)生、藥物、麻醉師、手術室、護士,甚至保姆。即把病患的身體交付出去,任由別人來主宰,來處置。這和他們生病前的情況是一樣的,永遠抹去了自己應該擔當和承受的責任。這責任就是,不斷地審核自我,不斷地校正人生,不斷地查尋存在的身與源泉的靈是否串通。
在我看來,我們的醫(yī)學專家、醫(yī)學院教授――更不要說一般非醫(yī)學專業(yè)人士和患者本人了――對疾病的理解是非常表皮和膚淺的,他們也許對疾病的生理、生化病理學有一定程度的思考和探討,也許只涉及疾病的近因、淺因和枝節(jié)因,而對疾病與形而上學、哲學、宗教、心理學、意識理論的關聯卻少有基本的連接與猜想。如果我們迷信那些健康長壽專家、那些患有科學控的醫(yī)學教授,聽他們的口氣,似乎他們已把生命、身體的奧秘弄得一清二楚,巨細無漏,仿佛神明。殊不知,這實屬一種狂妄,是因為受限、受蔽導致的無知使然。實際上,作為一種常識,每個人都應該清楚:與我們不知、應知的相比,我們已知的東西實在是少得可憐。就我們的身體而言,情況更是如此。所以對疾病,我們切不可妄加斷語,亂下結論,哪怕這涉及所謂科學的斷語和結論。因為所謂科學與非科學、或不能列入科學范疇的東西相比,實屬九牛一毛,滄海一粟。所以,對疾病的態(tài)度和對生命本身的態(tài)度應該是一樣的,即只能端以謙虛之態(tài),抱以敬畏之心。任何輕狂、魯莽的,唯物主義式的處置風格都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的。
面對物國的實際情況,我認為,疾病的心理學、形而上學、宗教哲學的追溯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因為現實的診療手段、醫(yī)治方式似乎已經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我曾經對我的朋友調侃地說過:“我的夢想是讓醫(yī)生失業(yè),醫(yī)院關門,藥廠倒閉,健身房消失。”有人說:這夢想太過無情,太過殘酷。我認為:不。其善良的動機就如同期望世界上沒有軍隊和監(jiān)獄一樣美好。請設想一下,如果沒有醫(yī)生,沒有醫(yī)院,這世界是何等地人道,何等地美妙!不過,這僅僅是夢想而已。
我非常痛心物國的這一事實:有疾病的逐漸升級,步步為營,但沒有疾病的可控之勢,緩減之態(tài)。我非常痛心現時的人們只知道明確的病癥,卻不知真正的病因。我更痛心人們患病之后所遭遇的那種被敲詐、被愚弄、被剝奪的悲慘命運。當然,寫出本文的初衷并不在于要去拯救、醫(yī)治別人,其首要的目的意在拯救、醫(yī)治自己。因為我始終堅信:人生有兩件事情是值得我們終身去關心與爭取的,這就是:身體的不病;心靈的不變態(tài),或者說不那么過分地變態(tài)。這是最起碼的要求,這是底線。如果說這兩件事情沒有做到,沒有做好,那就不要去奢談其他,比如,所謂的事業(yè),所謂的成功。
我認為,一個人首先應去關心的是他自己,應去拯救的也是他自己,此乃人生的頭等大事。就像自關心是真正的關心一樣,自拯救才是真正的拯救。我經常在想:要是一個人把自己給侍候、服侍好了,他就不需要別人來侍候、服侍了;要是一個人把自己給安頓、安排好了,他就不需要別人來安頓、安排了。正如瑞士文化哲學家讓?蓋普塞所說:“世界和人類的必要的改變是不可能通過世界改良者的嘗試來完成的;世界改良者們正如他們自己所說在為一個更好的世界而斗爭,但他們卻逃避了改善自己的任務;他們在玩弄一種司空見慣、雖然近乎人情但卻令人悲哀的游戲,即要求別人去做他們懶得動手的事;但他們所取得的虛假成就并不能減輕背叛世界以及他們自己的罪責。”
我認為,在物國,疾病是一種顯赫的存在,承載有特殊的含義。它不僅僅屬于醫(yī)學、生理學、生物學的范疇,無疑,它還暗含有更多社會學、政治學、哲學上的意義。在物國,我們甚至可以把醫(yī)學理解成存在學、神學,把疾病看作是某種贖罪與拯救的形式。我認為,與其把歷史看作物國人的信仰,還不如把疾病視為物國人的宗教。事實上,疾病早已成了我們的宗教替代品,成了我們生命關注的焦點,意義生發(fā)的中心,成了我們千言萬行的遞歸與心理指向的所在。
在一個荒誕的地方,與其說人們在適應社會,不如說人們在適應自己的不適應;與其說人們在生病,不如說人們在把生病當作宗教來發(fā)揮其作用,被迫擇其來作為意義的替代。因為沒有其他的悔過方式,其他的救贖之道,就只有通過疾病來抵償這種悔過與救贖。這就是為什么疾病會如此瘋狂的理由,為什么疾病會如此囂張的原因。 國人精神疾病呈高發(fā)態(tài)勢
我感覺,不知從何時開始,疾病就悄悄轉化了它的身份,成了我們的宗教,病房成了我們的教堂,醫(yī)生成了我們的牧師,看病成了我們的朝圣,而針劑與藥物則成了他們受洗的水與行彌撒的面包。疾病成了唯一與生命本體發(fā)生聯系的意義生發(fā)源與替代物,成了人們感受生命意義的主要途徑與唯一來源。盡管是一種負意義,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總比無意義強。所以,疾病是與意義問題糾纏在一起的。疾病是用來解決意義問題的。一般說來,那些意義均衡、意義自足、意義飽滿的人,不大容易生病。即使生病,也容易治愈。如果意義感匱乏,意義感欠缺,那生病很有可能就是回避意義(消極)或試圖解決意義(積極)的一條途徑。也就是說,意義感匱乏的人,多半就具有一種易病性人格的特征。為了減弱這種特征,恐怕意義感的生發(fā)與增加是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
疾病是物國人的承罪與贖罪手段,是物國人的悔過與補過形式。所以,從警示與贖罪的觀點看,疾病就成了物國懵鈍時代的大警鐘,病人是和平時代代我們言說的言說者,代我們反抗的反抗者,是以疾病這種特殊的方式在決絕尋求表達的表達者。所以,我們對疾病應存敬畏之心,對病人要抱以感激之情。因為疾病是一個文化機能失效時代的預警機制,是一個無民族的救贖形式。
健康的精神首先會反映在身體的健康上,好的文化肯定是首先會讓身體受益的文化。如果說,一個民族的文化貌似高聳在云端,放射出天國般耀眼的光芒,而民族很多成員的身體與面相卻又呈現出佝僂、猥瑣,那多半是文化被做成了鴉片的結果。一方面,吸食文化的鴉片,能滿足我們對文化的妄想;另一方面,又能使我們無視身體惡化的存在。這顯然是一種變態(tài)彌補法,魔鬼平衡術。我有時在想,反饋的程序是不是這樣的:首先是身體病人(發(fā)育受阻,進化中斷之人)炮制出一整套病態(tài)的文化學與審美學,然后,把這種文化學與審美學熬制成“營養(yǎng)針劑”對人體進行注射。最后,再通過這種注射產生精神病人(主要是精神妄想癥與精神匱乏癥病人)。接下來,又讓精神病人去復制出無數多的身體病人。就這么“身體病人精神病人身體病人”地來回倒,終成一種重復輪回的封閉循環(huán)。
正如伊萬?伊里奇所言:目前,身體的醫(yī)學化已經到達幾近流行病的程度了。生活的醫(yī)療化是廣義工業(yè)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使得所有普通人的好奇心、求知欲、沖突、放松、休閑以及創(chuàng)造性活動等都變得“有問題”,從而迫使人們四處求助“建議忠告”。這樣一來,那些專家們如律師、醫(yī)生、教授、顧問以及心理醫(yī)生便能在工業(yè)化和官僚化的(主/雇、醫(yī)生/病人等)關系軌道內發(fā)揮其效能:“醫(yī)療復仇女神”不僅僅是各種醫(yī)學分支的總和,也不僅僅是治療不當、馬虎大意、職業(yè)性冷淡麻木、政治權利的分配不當、醫(yī)學所裁定的殘疾以及其他所有因醫(yī)學實驗和醫(yī)療事故所引起的后果的總和,它的本質在于通過一種維修服務來剝奪人的自我應付、自我決斷能力;從而迫使人更臣服于“權―商”系統(tǒng),更好地服務于這個系統(tǒng)。
我們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方法,才能避免內在世界、私人空間的巨大損失,至少能過上一種身體不病、心靈不那么變態(tài)的生活?對一個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尼采曾經建議,為了避免這種損失,人必須通過對自身進行身體與語言上的實驗來實現自身的創(chuàng)造與提高。這是抵抗暴虐的公眾,抵抗現代社會全景式監(jiān)獄(米歇爾?福柯語)的強光,是極端的操練,目的在于奪回對自身主觀闡述的控制權,從而創(chuàng)造自己私人的自身形象。
我想說,人必須自覺地把自身當作自我塑造的材料,設法形成自己過正常生活的私人經驗。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存在論(或者說世界)本質上就是窺私癖,而道德說到底就是審美意義上的自我塑造。在攝影機、鏡子、玻璃幕墻、流行話語構成的無盡迷宮中,人必須通過自我重新闡述實現被監(jiān)視對象的重建,這恐怕是唯一的出路。換句話說,走出迷宮的唯一方法,就是待在里面――盡管很荒唐。人必須堅忍地接受安裝在現代制度上的諸多鏡屋,但要嘗試在千萬個映像當中,給自己的現實身份賦予某種反脆弱的風格。
我想說,倘若我們一味側重“解決問題”,恐怕難免錯失檢視內心更深處的契機。我們盡可以貼上心理學的膏藥來解決病癥,但如果不能探明并解決深層的病因,就難保癥候將來不會以另一種面目呈現出來。我認為,人我關系中的每個問題都是一種癥狀,表明的是你與內心更上游的源頭的失聯。事實上,每個心理困境都是助我們溯向上游、潛入深處的良機,問題的解決全賴我們是向內渴望和追溯,還是朝外依附和追尋。
我想說,只要曲解愛與被愛,導致的結果都是無愛,而無愛就是最嚴重的疾病。即使我們對最熟悉之人的愛其實也只是相對層面的愛,相對意味著一切隨條件狀況而變化,所以,人我關系不可避免是二元、對立、不連續(xù)、不穩(wěn)定的。但進入生命的最深層,我們就可以如實承認并接納一切,毫無保留、索求、批判與操控,率直面對自己生命的經驗,也因此而擁有一顆開放且覺悟的心。這里沒有你我的相對,任何地方、任何時刻,你都可以與任何生命靈犀相通而流露溫暖和開放。這種生命對生命的愛是絕對的、不設限的、無條件的。當絕對之愛的洪流在我們體內滾滾涌動,我們就能看到我們的生命自有其基本的尊嚴與神圣,并不需要仰仗外在的認可,于是再不會為饑渴(盼愛之來臨)和恐懼(怕愛之離去)而煩惱。在生命深刻的和諧中,我們深知:我們從來就沒有被傷害過,也不可能被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