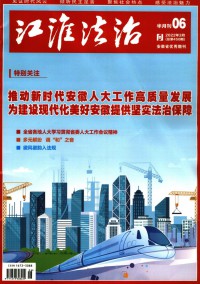法治方略對教育的啟發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法治方略對教育的啟發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良法的創制與合道德性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構建
從動態的視角而言,法治建設是一個從法的創制到法在社會生活中全面實現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法的創制是其邏輯起點。法治建設的形式要件首先是有法可依。沒有全面而周密的法律體系為人們的社會生活提供規范和保障,就難以使社會成員的行為符合社會所期待的“應該”和“必須”,社會生活就難以實現穩定有序。因之,在法治進程中首先必須十分重視法的創制。自我黨確立法治方略至今,我國已基本確立了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法律體系。正是這一系列法律的制定使得人們有法可依,從而為我國社會生活步入法治化軌道提供了前提條件。然而,作為實現法治國家首要環節的法之創制活動,還應進一步關注所創制的法的質量,即制定了何種性質的法律。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明確規定了法治必須具備的兩個要件:一是全體公民守法,二是全體公民所遵守的法律又應該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P81)按照現代法治理論,一部能夠被稱之為良法的法律,最起碼應表現為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對公民自由和權利的保障和確認。這意味著就價值論的意義而言,法治應該是良法之治。只有當公民認定其所面對的法律是良法、善法時,他們才可能守法,而如果他們所面對的法律在其價值評價中是劣法、惡法時,其行為表現就可能是避法、違法甚至抗法,從而法律之治、確立法治國家的目標就不免陷入空談。
法治必須以良法的創制為前提,這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實施具有重要的啟迪。即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我們不僅應關注其內容體系的構建,而且應進一步關注這種內容體系的合道德性。之所以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提出合道德性的要求,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社會所主導的特殊教育形式,它必須引領受教育者在面對多種價值體系時進行正確的選擇,也必須為受教育者設定應有的行為規范。而思想政治教育所昭示的價值體系和行為規范之所以能擔當引領受教育者的重任,不僅取決于其內在的合理性,更取決于其本身的合道德性。如果一種價值體系和行為規范對于社會進步和個人發展難以體現其積極的意義,那么它就難以滿足社會對受教育者的價值期待,從而也就沒有資格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在于其提出的要求在社會生活中的全面實現。這具體體現為其所昭示的價值體系被信奉,其所設定的行為規范被遵行,而這又是以這種價值體系和行為規范的道德合理性為前提。如果一種價值體系在道德合理性上存在缺失,一種行為規范對人的規約缺少道德上的依據,它們就難以得到受教育者的認同,從而也就難以在社會生活中實現自身。其三,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特殊的價值觀教育,必須得到受教育者的價值認同才可能內化為其內在的信念或信仰。而受教育者之所以在眾多價值體系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昭示的價值體系,之所以自覺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設定的行為規范的規制,是他們經過自身的思考和體悟后對思想政治教育所提出的要求的自覺認同,而這又離不開其對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道德合理性的認可。
二、司法工作者忠于法律的要求與教育者價值信仰的確立
在法治建設的過程中,立法階段所創制的法律必須經過法的適用方能實現自身的價值。而這種法的有效適用又是以司法工作者忠于法律為前提的。沒有司法工作者對法律的忠誠,就不可能有法律的有效適用。而將忠于法律作為司法工作者必須遵循的原則,是由當代中國的特殊社會背景決定的。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生活快速變化的時期。面對這種變化,法律本身固有的不周延性和滯后性特點決定了其和人們變化中的價值觀念不可避免的沖突。面對這種沖突,司法工作者是否應該堅守法律條文,這實質上是一個如何從更深層次理解司法活動之“應然”的問題。我們認為,司法自有它的一套程序,必須以法律為準繩。即使法律不怎么完美,甚至有瑕疵,但在修改法律之前,司法工作者必須依法辦案。馬克思在論證“法院該是一種什么形象”時也指出,法官是沒有上司的,如果一定要說法官有上司,法官的上司就是法律。這是對法院的獨立性和司法本質的深刻表達,也啟示我們應該對司法工作者提出這樣的要求,即當他們強烈地意識到自己將要執行的某項法律已經滯后于時展的要求時,他也只能犧牲自己的法律感覺,以服從法律的權威命令。因為,法律的價值在于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實現。如果每一個司法工作者都忠實地執行法律,那么,法之精神就能在現實生活中得以體現,法律所欲求的秩序就能達成。相反,如若聽任司法工作者在各自正義觀念的支配下各行其是,那法律正義就永遠無從實現,社會就會呈現出一派無法無天的景象,民眾也會失去預期自身行為法律后果的安全感。所以,為了法律的有效實施,必須對司法工作者提出忠于法律的要求。
這種司法工作者忠于法律的要求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在于,教育者必須確立并忠于與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一致的價值信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更為基礎和更具前提意義,也是更具難度的可能就是教育者價值信仰的確立。美國著名法哲學家、法律史家伯爾曼在談到確立法律信仰對于實現法治的重要性時指出:“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2](P15-16)同樣,教育者的價值信仰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的實現也至為重要。其一,教育者價值信仰的確立對于受教育者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悠久道德傳統的國家,也是一個極為重視榜樣作用的國家。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道德首先表現為一種“政德”即領導道德。先人認為,當領導者具有了良好的德性和人格,就會對全社會起到榜樣和示范作用。當下,思想政治教育者也應該成為受教育者的榜樣,這種榜樣是無聲的同時也是極為有效的教育。只有當教育者確立了堅定的信仰,受教育者信仰的確立才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其二,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價值理念的灌輸,其有效性不僅訴諸于理性,而且更多地是訴諸于信仰。如果受教育者缺乏對教育內容的信仰,就不可能將其內化并進一步轉換為外在的行為。而受教育者這種信仰的確立不僅要訴諸于教育內容的科學性和合道德性,也訴諸于教育者在信仰上的榜樣作用。很難設想,在教育者自身都對思想政治教育價值體系缺乏信仰的情況下,會令受教育者對其產生堅定的信仰。其三,中國不利于信仰之花生長的歷史和現實決定了確立信仰的必要性和難度,從而也決定了確立價值信仰的必要性。在傳統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著眼的是現實的人事,其極為務實的取向從客觀效應來說是不利于人們價值信仰確立的。并且,中國傳統的經濟形態是自然經濟,這種自然經濟作為一種和土地相交換而不是和社會相交換的經濟形態,也養成了人們務實的取向,這同樣是不利于信仰之花生長的。當下,中國的市場經濟還處于不盡完善的階段,市場經濟的逐利性、利益最大化原則和等價交換原則等極易對社會生活產生負面效應,而這同樣加大了確立信仰體系的難度。但是,不管有多大難度,教育者價值信仰的確立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積極面對的課題。因為,這不僅關乎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的實現,也是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思想政治基礎的內在要求。
三、法的權利本位與對受教育者利益的尊重
法治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自覺選擇的治國方略,其最終意義在于廣大人民群眾應有權利的實現,這也是法律的價值追求之所在。例如,刑法對罪與非罪的規定以及對犯罪行為懲處的明文宣布,其要旨在于為廣大社會成員提供一個生活和發展自身的良好環境,它體現的是對人的價值的關懷,對人的生命權、生活權和發展權的保護和確認;民法關于民事行為主體誠信原則的規定既是客觀上對中國傳統美德的一種強化,預示著立法者對誠信這一美好道德的向往,也是對民事行為主體應有權利的肯定;婚姻法對某些違法犯罪行為的規定和懲處,其目的在于維護人們追求家庭美滿幸福的權利。這啟示我們,法律雖然更多地是以剛性的“必須”來規定人們行為的底線,但其中對社會進步的追求、對人的幸福特別是對人的應有權利的關懷等內涵卻是極為豐富的。正是這種法律的內在底蘊,使得人們有可能對法律產生自覺的認同感,同時也促使我們應該以是否對廣大人民群眾權利的保障和確認、維護和發展的尺度去審視法律。法律就是對公民應有權利的確認和保障,法律運行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就是通過立法活動將這種應有權利規定為法定權利,再通過法的適用變為實有權利的過程。法之創制與適用的權利指向對于我們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依歸頗有助益。就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而言,培養受教育者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質是其重要的價值追求,因為這關乎社會的和諧穩定與全面進步。只有當受教育者確立了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質,其觀念和行為才可能和歷史發展的方向相一致,才可能滿足社會的價值期待。同時,實現受教育者的價值和滿足其利益需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和內容都應體現出對受教育者利益訴求的認可、尊重和追求,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實效的保證,也是其合道德性的體現。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這樣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教育者的“幸福之學”。這不僅因為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社會和諧穩定和全面進步本身就蘊含了受教育者的個人利益,是受教育者實現個人幸福的前提條件,也因為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獲得了正確的價值導向和行為規范,而受教育者這種正確的人生道路的選擇不僅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實現,而且本身就是其最大利益之所在。在過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我們往往忽視受教育者的利益訴求,甚至對這種訴求予以否定,這突出表現在將個人的正當利益當成個人主義而大加撻伐。這不僅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為令人生畏的活動,導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實現存在缺憾,同時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性出現缺失。這要求我們在現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是要將受教育者的幸福和利益實現作為重要的價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一個由多種要素組成的系統。其中,受教育者的幸福和利益實現無疑是不可或缺的方面。其二,要確認受教育者追求個人正當利益的合理性。只要受教育者對個人利益追求的行為沒有突破法律和道德的規制,其行為就具有內在的合理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對這種追求予以否定,而是應為其進行合道德性論證。當然,思想政治教育還有一個引領受教育者向更高層次邁進,即要求受教育者更多地關注他人和社會利益實現的問題。相信這種對受教育者利益訴求的關注,將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富人情味和價值合理性,從而也獲得了實現自身的可能性。
四、公民積極守法與受教育者對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自覺遵從
從最終的意義而言,法律必須在社會生活中得到公民的有效遵守方能實現自身的價值,公民的守法狀況關乎法治目標的實現。那么,法治社會的公民應該確立何種良好的守法道德呢?我們認為,對于公民而言,最為基本的守法道德是,不管他們對法律的理性認同程度如何,不管其在感情上是否接受法律,也不論他們具有怎樣的社會身份,居于何種社會地位,行為已達到什么樣的水平,面對法律,他們只應有一種行為取向——遵守法律,行為“合法”。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對守法主體往往表現為一種外在的強制,守法行為對公民而言往往表現為道德上的他律。所以,對廣大公民而言,還應進一步要求其將法律不是視為外在的強制,而是視為實現個人和社會價值理想的必要形式;將守法行為不是視作外在的他律,而是內在的自律,即把守法內化為一種道德義務。這不僅表明了公民守法層次的提升,而且直接關涉法律的實現程度。因為,“一項要求服從法律的法律將是沒有意義的。它必須以它竭力創設的那種東西的存在為先決條件,這種東西就是服從法律的一般義務。這種義務必須,也有必要是道德性的。”[3](P35)假如沒有服從法律的道德義務,那就沒有堪稱法律義務的東西,服從法律就僅僅是暴力下的被迫服從而已。如然,法律即使在一定的時期內得以實現,也絕不可能長久地為人們所遵行。
一種社會的法律體系要得到有效實施,必須以人們頭腦中自覺遵守法律的道德義務感為前提。這種對公民從消極守法走向積極守法、從強制守法走向自覺守法的要求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在于,應將受教育者對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自覺遵從作為重要的價值追求。其一,前已論及,當下中國的市場經濟還處于不盡完善的階段,其所固有的特點極易對社會生活產生負面效應。同時,市場經濟充滿著誘惑,這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施無疑是一種挑戰,使得人們堅守信念、行為不逾道德和法律之矩的難度加大,這就必然要提出受教育者對思想政治教育要求自覺遵從的問題。其二,從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來看,也要求受教育者的自覺遵從。思想政治教育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意識形態,對社會主義制度予以合理性的辯護。就其本質而言,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不是實證科學而是價值科學,為了維護現存的社會制度,它必須統一人們的信念,必然需要維護某種“輿論一律”。“統一”以至某種“單一”是意識形態不可少的品格。馬克思主義一旦成為意識形態,也就必然要履行這種職能,它必然有不可移易的政治價值觀。而這自然地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具有某種外在性,從而也就邏輯地要求受教育者對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自覺遵從。其三,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質而言,這種更多地訴諸于價值理念灌輸的活動對受教育者而言具有一種外在性,甚至這種外在性有時還表現為一種強制性。特別是當受教育者的認知水平還處于較低層次,價值觀念和思想政治教育所昭示的價值體系還存有差異,或者是受到自身閱歷和生活經驗的限制時,這種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外在性甚至強制性往往就顯得更為突出,這就自然地有一個要求受教育者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在理性上予以認同、在情感上產生共鳴、努力進行感悟和體味,并在此基礎上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自覺遵從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