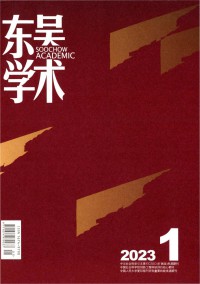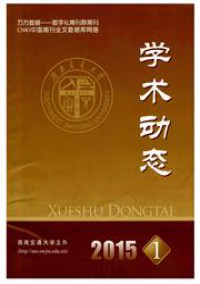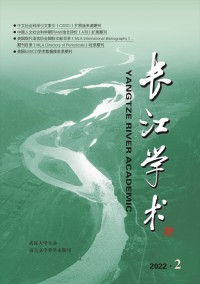學術和世變哲學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學術和世變哲學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晚清古文《尚書》辨真的非學術性動機
學術研究的主體是人,思想主張的提出是思想者與其身處社會互動的結果。晚清在古文《尚書》為偽的結論已為學界主流的情況下,突現一股辨真的高潮,也和社會變化息息相關。自乾隆中后期清代內部已經出現危機,道光后期英人來侵,從此清朝內憂外患不斷。社會的急劇變化引發學人思考,他們將學術研究與自身對國家前途的擔憂結合起來并試圖通過這方面的努力找尋挽救危亡之路,這一時期,有學者出于對國家軍事情況的擔憂,集中力量研究邊疆史地,已被學界視為鴉片戰爭后社會變化在學界的投影。與此類似,晚清以來的辨真活動同樣也是“學人”對“世變”的回應。他們看來,道咸以來中國在內政外交上的節節失敗根源乃在“人心”淪喪。光緒二十一年洪良品在給美國傳教士李佳白的信中說:“中日之戰,非兵不強,非餉不足,實由人心邪佞,比黨誤國之所至。”“核實之道,在于先正人心,人心不正,雖以一人精西學,不過如洋報所斥行私各弊,仍無補于國家,人心茍正,舉中國圣賢之法度,循而為之,修攘亦有余。”[12]而作為“世道人心”立論基礎的古文《尚書》,成為這些學者維護的首選。
以洪良品為例,洪良品(1827—1896),同治七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江西道監察御史、戶科掌印給事中等職[13],他為古文《尚書》辯護之因,體現在其《古文尚書辨惑》的著作原委上。據該書《跋》,此書和某“上疏欲廢古文者”有關。民國初學者倫明認為此人即王懿榮,其上疏在光緒十年:“其后懿榮疏被駁,良品疏亦不果上,遂發奮撰成此書”。該《跋》落款為光緒十二年,是該書至少當年已經成形。如洪氏光緒十年著作,至十二年正好三年,而十年恰是王上疏年[14]。洪良品稱:“古文為圣道圣學之所寄也久矣,自漢魏六朝以至隋唐……是綱維乎,是無從稍有訾議其間者,乃更數千百年忽以末學膚受,自作聰明,以孔子手定之書妄被以偽孔之名,誣圣毀經,莫此為極,此固有心世道者所必起而發憤與爭,固不獨駑質下材為之矻矻力辨也歟?”[15]這樣的著作動機,也是歷來辨真學者的共有特征,且言辭之激烈,隨時間推移,與社會動蕩和國力下降的速度成正比。
乾隆間曾有廢古文之議。當時莊存與提出:“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戒亡矣;《太甲》廢,‘儉勤永圖’之訓墜矣;……今數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后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16]尚能較心平氣和。而道咸以來的古文《尚書》辨真,則由于這些學者身處的環境,不再是四海升平的“盛世”而是國力急劇下降的時代,故體現在這時的是對“世道人心”更為焦慮的思考。
咸豐六年王劼寫道:“使謨無大禹,則惟精惟一之心法不著,不分盆稷,則盆稷之功用不彰,失此宏綱,經義晦矣。況《仲虺之誥》、《大甲》、《說命》,皆君臣之所以相須,若以微子之賓賢,蔡仲之嘉德周官之大明黜陟以及《君陳》、《畢命》、《君牙》惟爾惟公,予一人膺收多福者概變置焉,將使君道日就昏亂,人心世道日就詭隨,而曰以復古學,復古學何為哉!”[17]與洪良品同時的吳光耀在《古文尚書正辭》中則說:“奚是乎《正辭》?以好異甚則心術壞,世變可悲也。”[18]民國初王小航在所組織的衛經社中強調:“請觀乾隆以來百數十年,世風日降,人心日肆,以至無可收拾,此一代人之獨智者,于人心世道果何如耶?則知詡小慧以毀諸經,昧心害世,不過互相倚傍以惑浮名,遂至貽害天下而不顧也,今我同人有志衛經,原不限于一經,而毀經諸說,尤以毀古文尚書為最烈,故衛經應以是為先。”[19]
二、問題的提出
作為一部經歷了秦火劫難、命運多舛的典籍,《尚書》為后來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空間和話題。“《尚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于《洪范》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于《禹貢》之山川;明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于今文、古文之真偽。”[1]其中古文《尚書》真偽問題是學者關注的焦點。一般認為,宋代吳棫最早展開疑辨,其后朱熹、吳澄皆有懷疑,明梅鷟提出二十五篇古文及孔安國《序》是后人“蒐括群書,掇拾嘉言,裝綴編排,日鍛月煉,會粹成書。”[2]清初閻若璩認為孔壁中有16篇真古文,馬融、鄭玄皆見并作注,然此本永嘉之亂時亡佚,東晉梅賾所上25篇為偽書。此結論受到后來學者高度評價,視為定論。
既然閻氏已做出如此不刊之論,在他之后的考辨,就應呈現出一邊倒情景。然而通過對《尚書著述考》[3]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和《四庫未收書輯刊》等幾部主要叢書中的檢索,我發現有清一代,與轟轟烈烈名家輩出的辨偽活動如影隨形的,是一股不絕如縷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出現高峰,集中出現了如洪良品《龍岡山人古文尚書四種》(包括《古文尚書辨惑》、《古文尚書釋難》、《古文尚書析疑》和《古文尚書商是》)、《古文尚書賸言》,王劼《尚書后案駁正》,張崇蘭《古文尚書私議》,謝庭蘭《古文尚書辨》,吳光耀《古文尚書正辭》,張諧之《尚書古文辨惑》等一批辨真著作。但是,因對“古文《尚書》非偽”結論的不屑,學界雖注意到這一時期辨真諸說的存在,如梁啟超說“當時毛奇齡著《古文尚書冤詞》以難閻,自比于抑洪水驅猛獸。光緒間有洪良品者,尤著書數十萬言,欲翻閻案,意亦同此。”[4]蔣善國對清代的辨真文獻作了更詳細的列舉[5]。隨后劉起釪在《尚書學史》中專辟一節,將這些辨真文獻分為“堅持偽古文非偽的”和“知其為偽書仍要維持其經典地位的”兩種。[6]卻對這種現象的形成原因與特質少有研究,或僅簡單歸為“為搖搖欲墜的后期封建統治者效命”或“迷戀骸骨”。[7]目前學界的研究取向有兩種。一種延續傳統觀點。如楊緒敏仍稱辨真著作為“迷戀骸骨”[8]。另一種則重新審視真偽問題的討論。如劉人鵬對閻若璩辨偽論據提出質疑。[9]葛兆光先生也認為“不必特意把‘史料’看成是‘真’與‘偽’,更不必把‘真’與‘偽’分出價值的高下,無論真偽,它都包含著思想的歷史。”[10]
總體來說,學界對辨真文獻似重視不夠,或許是認為這些“迷戀骸骨”的著作不值一提,但為什么有那么多的學者要寫作這些可能在學理上并不成立的著作?我們以往的研究主要將視野集中于辨偽文獻上,是不是將歷史簡單化了?在這些辨真文獻的背后,究竟展現了怎樣的思想世界?“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術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11]
三、以對“虞廷十六字”的考辨為例
所謂“虞廷十六字”是指《尚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幾,允執厥中。”這十六字是程朱理學理論體系的源泉,對將理學作為功令的清代國家來說,更是進行統治、維系世道人心的重要根據。閻若璩認為此出于《荀子》所引《道經》:“《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遂隱括為四字,復讀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偽古文蓋如此。”而洪良品則說十六字精妙絕倫非荀子所能道:“虞廷十六字,古相傳為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荀子之學醇疵參半,豈能體驗及此而造語如是之精密哉?”[20]
關于這個問題,辨偽學者多認為晚出古文成于后人湊集,“搜尋晚出二十五篇之文詞之來源,并指出其湊集之破綻。此實占攻晚《書》者之工作之大部分。”[21]而今天學者大多在肯定辨偽派“晚出古文《尚書》為偽”這一結論的基礎上,贊賞他們的研究。但是也有不同聲音,如楊善群認為同舊籍引語相比,古文“完整、全面”、“連貫、流暢、自然貼切”。“古文《尚書》決不是‘搜集’引語編造出來的,而是別有來源的真古文獻。”姑且不論古文《尚書》是否別有來源,僅就“同舊籍引語相比,古文‘連貫、流暢、自然貼切’”[22]而論,實際上恰好支持了古文《尚書》乃后人蒐括群書會粹成書的假說。值得注意的是,廖名春利用郭店楚簡和馬王堆帛書提出“簡文所引出于《大禹謨》而不見于‘晚書’《大禹謨》篇。這一事實,對于討論‘晚書’的真偽很有啟發。”[23]這一利用地下材料作出的論斷,基本可以證實晚出“古文”成于后人,非先秦舊本。
但在閻若璩著作已廣泛流行的晚清,為何學者還要維護這個在學理上并不成立的“道統”?這主要是和晚清特定的時代有關。辨偽派學者大都生活在清前中期,和道咸時代相比,這一特殊的歷史環境雖然也有維護世道人心的要求,但遠不如后者強烈,造成考辨雙方在出發點之不同。辨偽學者雖也承認古文《尚書》至高無上的地位,但主要是將其視為一部可供研究的先秦典籍。在他們看來,對這部典籍進行甄別,以考究其真偽的學術活動,其意義遠大于維護所謂偽孔學道統。閻若璩一方面承認自己“得罪于圣經而莫可逭也”,另一方面仍堅持“荀子因有言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余之疑偽古文也,正以其信真圣經也。”這種“以經學方法重新審視理學系統的主張,無異于把程朱理學推到文獻考證的學術法庭。”[24]而與辨偽派求真、求實的純學術興味不同,在辨真學者筆下對古文《尚書》的學術研究,不再是一人一時書齋中的考證功夫,它關乎與整個國家的命運相關。
所以,辨真派首先強調這十六字乃是二帝三王統治之大法,不可能為偽,其次才進行學術上的論證。洪良品說:“虞廷十六字古相傳,為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荀子之學醇疵參半,豈能體驗及此?”[25]張諧之則認定:“夫圣賢之道統,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也,道統若滅,則生民將近于禽獸,即天地亦無所恃以立也,閻氏縱不為生民計,獨不懼近于禽獸乎?……非病狂喪心者耶?”[26]不僅辨真派,還有一些學者,雖未參加對古文的考辨,也積極從維護世道人心的角度認為古文不可廢。如夏炯認為,閻若璩攻擊古文太過:“以為無一字不從繳襲而來,則肆妄未免太甚。……古文之真偽未必能遽必,即使真系偽撰,其文辭古樸、義蘊宏深,古先圣王之遺訓微言亦賴以不墜,歷代以來朝廷頒置學官,儒者奉為佳臬,閻氏試自問所學能窺見此中之萬一乎?”(《夏仲子集》卷三,《書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后》)。
在今人看來這樣的一種應對方案,無論是和“師夷長技以制夷”還是戊戌時期變革政治制度的嘗試相比,都顯得不合時宜。甚至也不能和“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頑固主張相提并論。因為辨真學者再三致意的“道統”的基礎——“虞廷十六字”乃是偽造的。這也就是現今清學史在論及清代《尚書》學時,往往視域集中在辨偽學者及著作上,而對辨真則多一筆帶過的原因。但對史家而言,歷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歷史上的客觀存在,探討原因說明意義,而不是用“后見之明”預先褒貶史實。具體到本文,對今日的研究者來說,否定辨真諸說可以理解。但同時也要看到,歷史的發展充滿了歧出性和復雜性,特別當我們回首整個晚清史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無論是在洋務運動時、戊戌維新中,還是辛亥革命后,都有一股強大的、主張從中國文化自身尋找救亡圖存的手段的主張。晚清古文《尚書》辨真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歸入其中。
參考文獻:
[1]《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二《〈日講書經解義〉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第1版。
[2](明)梅鷟:《尚書考異·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版。
[3]許錟輝:《尚書著述考》,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年版第1版。
[4]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梁啟超論清史學二種》本,第12頁。
[5]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00頁。
[6][7]劉起釪:《尚書學史》,中華書局1989年第1版,第361-370、366頁。
[8]楊緒敏:《中國辨偽學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9]劉人鵬:《詮釋與考證——閻若璩辨偽論據分析》,載《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年第1版。
[10]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29頁。
[11]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
[12](清)洪良品:《三復李佳白書》,載《龍岡山人全集》,光緒中稿本。
[13]馬延煒:《鄂人洪良品的生平與著述》,《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6期。
[14](清)王懿榮:《請復古本尚書附入十三經注疏與今本并行疏》,載《王文敏公奏疏稿》,宣統三年江寧印刷廠排印本。
[15][20][25](清)洪良品:《古文尚書辨惑》卷首、卷七,光緒十四年排印本。
[16](清)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第二輯《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武進莊公神道碑銘》,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
[17](清)王劼:《尚書后案駁正·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1版。
[18](清)吳光耀:《華峰文鈔》卷三《古文尚書正辭·自敘》,民國間鉛印本。
[19]王小航:《衛經社稿·自序》,載《水東集初編五種》,民國十七年刻本。
[21]張蔭麟:《偽古文尚書案之反控與再鞠》,《燕京學報》1929年第5期。
[22]楊善群:《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第4期。
[23]廖名春:《從郭店楚簡和馬王堆帛書論“晚書”的真偽》,《北方論叢》2001年第1期。
[24]趙剛:《論閻若璩“虞廷十六字”辨偽的客觀意義——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哲學研究》1995年第4期。
[26](清)張諧之:《古文尚書辨惑》卷二,《四庫未收書輯刊》3輯5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
論文關鍵詞:晚清;古文《尚書》;辨偽;辨真
論文摘要:一般認為,對古文《尚書》之偽的認定經幾代學者考辨,由清初閻若璩基本完成。但在古文《尚書》之偽已成學界主流觀點時,仍然存在著一股雖然微弱卻不絕如縷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呈現出特有高峰,集中出現一批辨真著作。學者們之所以寫作這些在學理上可能并不成立的著作,乃與他們對晚清中國衰敗原因實于“世道人心”之淪喪的認識有關。學術研究受到了社會變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