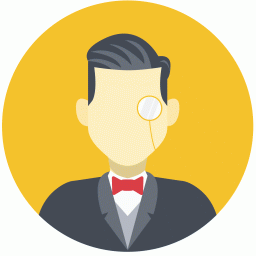批判的恢復哲學思考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批判的恢復哲學思考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文壇的歷史和文學的現實顯示: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要在吐故納新中走向現代化,離不開對人類生存的歷史與現實的理性審視與批判。本文在對《羊的門》的主題意向的剖析中,認為這種批判應體現在對世俗政治批判,人性批-y4和文化批判三個層面上。
關鍵詞:世俗政治批判人性批判文化批判人文精神價值理性
應該說,從{o年代后期開始的歷史“轉折”,到so年代中期,“轉折”的意義已基本上完畢其對于文學創作的影響表現為新時期文壇以追尋人道主義價值理想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高揚,表現的形態是啟蒙和批判,尤其是情感的和理性的批判內容與力度,貫穿于這一時期的整個文學思潮之中。隨著歷史進入另一種意義上的社會“轉型”,“轉折”時期的歷史慣性在價值理性層面上的滑行遭到逆轉,工具理性上升到主導地位,文學創作開始邊緣化。敘事姿態呈現出無奈和反諷,敘事視野轉向歷史和個人,那種干預現實的批判精神開始消隱。可以說八十年l弋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的十年是缺乏“批判”的十年,是文學整體上對現實回避與妥協的十年,即使成功之作如《心靈史》、《白鹿原》者亦概莫能外。如果說《抉擇》、《蒼天在上》等作品和“現實主義沖擊波”的震撼給世紀末的文壇帶來了直面現實的若干亮色,但這些作品執著于世俗層面的關注卻又給批判意識的重新崛起和文學重返“中心”的努力蒙上了一隱晦暖昧的外衣。文壇的歷史和文學的現實顯示: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要在吐故納新中走向現代化,離不開對人類生存的歷史與現實的理性審視與批判,正是在這一點上,李佩甫的長篇新作《羊的門》以顯示了批判主題的恢復而彌足珍貴。
《羊的門》的出現無疑是世紀末文壇的一件大事,是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文學創作重返社會中心努力的碩果,其冷峻的現實主義品格來自作品理性的、多向度的批判鋒芒,重新接續了八十年代文學創作的批判主題,從而恢復了先鋒文學等創作思潮對它的疏離和解構。《羊的門》批判主題的深刻性和多向度性體現在世俗政治批判、人性批判和文化批判三個層面上:
對政治世俗化的批判是《羊的門》批判主題的最外層部分。文學歷史走到二十世紀的盡頭,《羊的門》顯然已擺脫了八十年代初單純的政治批判模式,而將批判的矛頭直指現實生活中的世態炎涼,宦海沉浮。小說于客觀冷靜的描述與審視中摒棄了世俗化的和光同塵,懸置判斷的同時卻顯示了熱得發冷的批判激情。呼國慶兩起兩落的官場經歷揭露了當今權力系統中獨裁專制、勾心斗角的驚人現實。呼國慶和王華欣的權力斗爭以范騾子的升遷和呼國慶一一謝麗娟的情感糾葛為核心內容,以權力的爭奪與反爭奪為最終目的。在王華欣身上集中體現了權力系統內部世俗化的目標追求和追求手段的殘酷性。他在“一號車”事件中為維護自己在穎平縣的絕對權威而向呼國慶發難,抓住呼國慶處理范騾子行賄一案的不夠冷靜,在情感問題上的道德失衡及違法行為,利用范騾子的求升心理,力圖置呼國慶于死地而后快。政治價值判斷的神圣性和莊嚴性所體現的意義在這里已喪失殆盡,有的只是對諸如權力、名譽、地位等世俗利益的不擇手段的追求。而縣長呼國慶的行為在維護個人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相對地被作者賦予了一定的合理性和正義性,如揭發范騾子的謀官行賄,搗毀王華欣支持的“造假村”等,但他在處理與謝麗娟的情感糾葛上卻屢屢失策,幾乎被對手逼人死角,雖有呼天成的相助而最終轉危為安,遺憾的是他的行為策略并沒有擺脫世俗目標的牽引。費盡心機撮合妻子和秦校長的婚外戀以求達到離婚的目的,重用范騾子和搗毀蔡花枝的二造假村”是為了打擊王華欣的勢力基礎,傳統的倫理道德標準和理性的公仆意識在他身上也難以找到立足之地。從呼國慶的仕途起落中不難看出:光明正大的政府行為和暖味陰暗的個人動機糾纏在一起,有益民眾的局部合理性和違法亂紀的全局荒謬性難以區分,正義的動機和行為常常需要借助非正義的手段才能達到其目的,由此造成現實政治生活面貌和行為的諸多無序性和不合理性。《羊的門》不動聲色、懸置判斷的敘述策略給讀者造成了一種驚心動魄的反面效應,從而在世俗的層面上達到批判的目的。
按照批判的對象范圍區分,《羊的門》中的人性批判又要分為普遍的共性批判和有概括性的個性批判。對在歷史和現實中形成的人性現實缺憾進行深人靈魂的剖析和批判是《羊的門》批判主題中最主要最有價值的部分。現實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現實,現實生活具象所呈現的共時性特征,正是歷史生活發展中歷時性積累的結果,故而《羊的門))在剖析人性弱點的同時又滲透著對其歷史成因的言說。
《羊的門》的最大成功在于塑造了呼天成這個集中國幾千年人治文化于一身,又能賦予其現代性表現的人物形象,而這個平原統治者的誕生基礎是許地平原民眾的愚味和人格的屏弱。《羊的門》以編年體方式列舉了許地所歷經的天災人禍,而他們得以頑強繁衍生存下來是因為“平原人是活小的”,該地是一塊.‘綿羊地”,一塊.‘無骨的平原”,那以柔弱、萎縮為特征的平原上的二十四種草正是該地人缺乏強健人格力量和獨立自主意識的寫照。險惡的自然往往是檢驗人的生命力的尺度,平原人對..屋”從形式到內容的營造與崇拜,則表現出他們面對來自自然和社會的災難和壓力缺乏抵抗的自信,只能憑借.‘屋”來茍安一隅,來遮護他們萎縮的生命力,這種病弱的人格與強烈的依賴感必然導致思想意識上的盲從,從而造就了滋生專制統治的溫床C從《敗節草》到《羊的門》,我們可以看到作家對這種以“小”活人的生存態度和生存方式的體認和深化。這種生存態度和生存方式以柔弱無骨為基本特征,以隱忍退讓為行動前提,一旦與強有力的權力或意識權威相遇,只能.‘俯首稱臣”,自主意識和創新精神在這里已成奢求,誰掌握了它們,誰就是平原的統治者。
如果說魯迅當年執著于麻木不仁、愚味落后的國民性批判是為了拯救苦難之中的國人的靈魂直到苦難之中的國家民族。《羊的門》對平原人萎靡退縮、安于現狀的人性批判則尖銳地指出了社會現代化過程中人的現代化問題。呼家堡可謂富裕之村,但我們不說呼家堡是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村鎮。呼家堡的村民總體上根本不具備現代化社會對“人”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即人的獨立自主,從物質到精神的全面獨立。從物質上說他們富裕,而精神上則是赤貧。呼家堡物質現代化的程度很高,可在呼天成的思想禁錮下,人們的思想趨于凝固僵化,除了呼天成外呼家堡沒有第二種聲音,能夠體現精神自由程度的處理個人擁有物的自由被相對剝奪,而人們竟安心于、甚至沉醉,留戀于這種被剝奪。當代表.‘最高聲音”的呼天成病倒后,呼家堡人因失去思想中心而不知所措。小說結尾那片令人心顫、令人心悸的狗叫聲,不能不讓我們懷疑這是否是正在走向現代化的“人”。李佩甫不動聲色地將筆觸伸人他們的靈魂,剖析他們的靈魂,在剖析中引導我們深思產生這種病態人格的歷史,在歷史和現實的契合點上思索’‘人”的未來。
普遍性的人格萎縮必然導致專制與極權,以此為界,可以探究中國歷代統治者推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內在根源。《羊的門》的核心人物,呼家堡的主人呼天成正是該地這塊“綿羊地”上成長起來的極權政治家,一位.‘東方教父”式人物。在繼承傳統專制文化的基礎上,作者又賦予其現代性表現,二者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進人呼天成的行為策略中,構成其“外圓內方”的行為模式的依據,顯示了李佩甫對歷史與現實交匯的世紀末中國文化的冷峻審視。
呼天成“外圓內方”的行為模式建立在對平原人格心理積淀和權力系統操作方式深人體認的基礎上,主要由他的外交策略和統治策略加以體現。外交策略的“圓”結構由經營“人場”和以“小”活人兩種策略方式為支撐點。經營“人場”為目的是打開外向渠道,靈活社會關系,為呼家堡尋求背景支持。呼天成在中冒險救下被打傷的省委副書記老秋,先后培養出邱建偉、范炳臣、馮云山等省界要員,為呼家堡的日后興盛提供了外圍保障;與經營“人場”相反相成的是以“小”活人的處事策略。有了強大的背景支持,呼天成并不頤指氣使,處處以“玩泥蛋的”自稱,避免顯山露水。在處理車禍事件及王華欣、秋援朝、李相義對呼家堡的“訪問”中充分展示了這種以守為攻、以小抑大、后發制人的處事策略,反映了他對中原大地人格文化、民族心理積淀的精度提純以及對外交行為中“小”與“大”的關系(“大象無形”)的辯證認識。但這一切不僅僅是浮在表層的幻象,僅僅是一種手段,一種外交方略,其根本的目的是為了樹立呼天成在呼家堡的權威,鞏固呼天成在呼家堡的統治,并最終成就了他“四十年不倒”的名聲。
在取得背景支持的同時,呼天成對呼家堡實行了“內方”的統治策略,由物質控制與精神禁錮兩方面構成。如果說“外圓”尚顯出呼天成性格中溫情的一面,“內方”的統治策略則以冷酷強硬為主要特征。呼天成動用強大的外援儲備使呼家堡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同時又強化了對村民的物質控制。為保證呼家堡日常機制的正常運行,呼天成制定了從生產到生活各方面的,花樣繁多的制度,強調整齊劃一和絕對眠從。跑外交的王炳燦因在推銷過程中私收禮物而未及時向呼天成匯報,被勒令在眾人面前一再,’洗手”,直至被撤職反省。冷酷的物質控制造成了呼家堡經濟繁榮背后的精神貧乏和人性畸變。與物質控制相聯系的是精神的禁錮和奴役。呼天成自在制止盜竊事件中小試牛刀后,便著后開始控制村民們的精神世界。通過“斗私會”,籌建絕對模式地上和地下新村,“展覽臺”等一系列事件,打破村民之間長期固有的血緣人倫關系,利用村民對虛榮的畸形追求激發所謂的“工作熱情”,將村民們的思想以物質的形式統一化、凝固化。樹立思想權威的另一面是對異已思想進行亨J擊,這集中體現在呼天成與孫布袋之間長期控制與反控制的暗地較量上。呼天成為控制一心想抓自己把柄,推翻自己思想統治的孫布袋,竟讓布袋的妻子、自己的情人秀’(屢次赤身裸體,自己則靜坐一旁練功,利用布袋的捉奸企圖,與孫布袋展開長期的心理較量,以培養自己控制情欲的意志和能力,毀滅自己的人欲而求建立一種“神性”。此外,利用母喪以身作則打擊外來宗教影響,利用秀丫作誘餌打擊“革命”的八圈,在孫布袋死后仍讓秀丫在其墳前脫光衣服的“報復”等,都只能說明呼天成在追求極端權力人格的過程中人性的畸變,而非什么“神性”。
“外圓內方”的行為模式并非呼天成的獨創,而是古往今來的為人處世哲學和專制統治思想在呼天成身上的融合、凝聚和具體化,因而對于呼天成這種行為策略的最終的利已主義動機的剖析無疑呈現出某種普遍性,這種具有極強概括力的個體人格展覽,則顯示了具有共時性特點的政治權力運作中正常人性難以避免的失落。
對傳統“人治”文化批判是李佩甫在《羊的門》中追求的最高批判境界。如果說對世欲政治層面、人性層面的剖析指涉的僅是形而下意義的批判,顯得缺乏文化背景和淵源,需要作形而上的提升,那么提升的結果便是對于穿越歷史和現實的“人治”文化的批判,這是《羊的門》批判主題超越世俗、人性層面達到的最高層次。
“人治”文化在中國擁有源遠流長的歷史,長達兩千多年的帝王專制便是這種文化的獨特體現。“人治”的諸多措施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制度化、模式化,最終上升為一整套的統治理論,用于指導帝王將相、諸候王公的統治實踐,并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深深積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以其超常的穩定性和歷史惰性牽制著邁向現代化的步伐。呼天成正是這種文化的現代性載體,其“外圓內方”的智者行為策略深得“人治”之神韻,融合了權力系統的現代運作方式和傳統的處世哲學,在外交內政兩方面相得益彰。正因為如此,呼天成才能先后擊敗縣地兩級最高權力者,在平原上縱橫摔闔,在現代社會的權力網絡中游刃有余、來去自如;成為平原大地上的精神領袖,一位典型的“東方教父”。
與此同時,必須看到,人治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專制文化,只不過在現代社會中因罩上耀眼的物質光環而具有了現代的表現形式,其本質仍是傳統的。中國社會長期的帝王統治史和政治斗爭史及因此而推廣的愚民政策導致的國民精神的屏弱,為它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遺憾的是在《羊的門》中讀者仍未看到這種情況的改觀,封建共產主義式的呼家堡并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社會縮影,其內部現代的專制統治導致的是人民思想的停滯,人格的萎縮乃至人性的退化,而呼天成最后還堅持認為呼家堡是“一塊凈地”。與此同時,這種人治觀念在現實政治層面運作時表現出的拋棄道德和倫理價值標準的極端世俗化形態,都表明這不僅僅是個體思想認識上的悲劇,更是文化的悲劇—歷經傳統和現實的文化悲劇。“現代化”的最終目的是人的現代化,以此為尺度來衡量人治文化在中國社會邁向現代化過程中的影響和作用,只能是一種阻礙,一種栓桔,一種對民族精神的開拓與提升的壓抑和傾軋。
四
批判的目的是為了建構。《羊的門》以其批判主題的深刻性和多角度性堪稱一部“人民批判書”。冷靜的敘事姿態和批判的敘事精神之間的背反賦予小說文本以極大的張力。難能可貴的是小說并沒有將意義終止在批判的層面上:呼家堡村民劉庭玉的堅持出走,孫布袋顛覆權威的持續努力,呼國慶對呼家堡繼承人位置的放棄,都能于思想的窒息中給人以振奮和希望。《羊的門》不可能提出根治傳統人治文化瘤疾的有效途徑,但通過批判顯示出了其基本的建構意向:人格的獨立和人性的健全乃是人的現代化的基本前提,而獨立人格和健全人性的培養同樣需要適合它發榮滋長的土壤。《羊的門》的出現顯示了八十年代文學批判話語在世紀末文壇的恢復,以批判的激情續接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當代文學重返社會中的努力,標志著歷史理性的現實(而非世俗)關懷開始并正在當代文學中重新尋求它的棲身之地。這正如謝冕所說的:“文學若不能寄托一些前進的理想給社會人心以導引,文學最終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著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