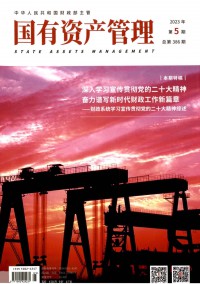國有資產轉換管理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國有資產轉換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朗咸平的觀點引來多方爭論,各種觀點交匯碰撞,我認為焦點是兩個,一個是國有資產要不要轉換所有制形式,將其賣給特定的私人,比如原公司的管理層或者職工,或者是其他愿意出錢的人。另一個是如果要做上述轉換,如何運作;也就是如果要賣要分,怎么賣怎么分。
一、要不要對國有資產進行所有制轉換
1.企業國有在分配上的優越性
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建設,這種制度的出發點就是滿足全國人民而不是少數人的利益,也正因這一點,全國人民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那么,如何更好地滿足全國人民的利益?假設有一筆1000萬的生產性資本,一種情況是國有,另一種是私有,一年后都產出了1200萬的銷售收入,那么毛利潤都是200萬;這時,如果這筆資金是國有的,國家可以把這200萬全部收歸國庫、作為財政收入;而如果這筆資金是私有的,國家就只能收回200萬中的33%企業所得稅和20%股息紅利類個人所得稅,大概為100萬,作為財政收入。我們顯然可以得出結論:當資產利潤率或者說投資回報率一樣時,國有資產對于國家財政的貢獻比私有資產大很多。當然這個模型十分簡化,忽略了擴大再生產等等因素,可是不影響我們的結論。
所以說,從國民財富分配的意義上說,國有制顯然比私有制更對廣大國民有利。當國家通過國有制多收入了100萬后,可以拿去辦奧運、建公路、辦大學、辦敬老院;而如果那筆資金是私有的,國家就拿不到多出的那100萬,那100萬就名正言順地完全歸那位私人老板所有,她如果愿意發善心,再捐出50萬給國家修路燈,那我這個普通國民當然歡迎;可是,她如果按照法律規定交完了稅后就一毛不拔了,我也沒有辦法。美國最富的1%的人口擁有全美總財富的37%,我可不希望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有人會說:“雖然公有制下國家的財政收入也許比私有制國家多,但是政府拿著那么多錢怎么花,我一個平頭百姓沒有說話權。比如我認為對于奧運冠軍只能獎勵10萬,但國家要獎100萬;我奶奶住在敬老院,我認為我這個城市的敬老院應該每年得到100萬的財政撥款,而不是現在的50萬,可是我的話沒有人聽。”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國家如何傾聽國民的意見,如何將財政收入在不同國民的不同需求之間進行輕重緩急的分配。但不管怎么說,政府財政收入200萬而不是100萬,肯定對于廣大國民更為有利(但對資本家不利)。我想,這就是我們當初全面實行國有制而不是私有制的一個主要原因。
2.企業國有在效益創造上的弊端。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逐漸發現當初的考慮并不周全。如果不論國有私有,投入1000萬生產資金都能有1200萬的銷售收入,那當然我們都傾向于企業國有(除了少數潛在的資本家)。可是,如果在企業私有的情況下,投入1000萬能有1200萬的銷售收入,國家能因此有100萬的稅收;而在企業國有的情況下,投入1000萬只能有1010萬的銷售收入,那么即使我們一分錢都不去做擴大再生產,而將毛利潤全部上交國庫,也只有10萬。如果是這樣,我們也許會想:是不是企業私有對大家更有利?這當然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模型,可是,這一假想性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實的。
建國以后,歷經反右、三年自然災害、等,都是“階級斗爭為綱”,大家忙于相互間的革命斗爭,沒有什么心事搞經濟建設。終于結束了“”,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家卻發現國有企業效益總是難以提高。雖然學校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說計劃經濟體制比市場經濟更能提高效益,說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會周期性地出現經濟危機。可是事實勝于雄辯,反正大家就是感到國有企業經營起來總是別扭,效益總是上不去,乃至虧損。于是在1980年代搞承包制,但導致了企業短期行為嚴重。到了1990年代,國有企業的效益低下問題日益嚴重,此時,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已經是如何解決國企的生存問題。當時,出現了很多虧損的國有企業,甚至需要靠銀行貸款開工資,這些國企不僅不能為國家創造財富,還成了國家的包袱。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地方政府將地方國企賣給民企的現象。
到今天,國有企業效益低下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2003年1月3日《中國經濟時報》報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說:國有工業占工業總資產的一半,占總工業貸款的三分之二,卻只創造了工業總產值的三分之一。這種局面長期不改變,必將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中國企業家聯合會和中國企業家協會作出的“2004中國企業500強”報告顯示,在資產利潤率方面,500強中的民營企業和港澳臺外資企業,分別比500強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高出5.57倍和10.19倍。更重要的是,500強中的這些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大多集中在行政壟斷性行業,比如電信、鋼鐵、石油、電力和石化等,它們能賺錢,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行政禁止民營企業進入這些領域得來的,沒有得天獨厚的行政資源,實在難以說它們就能賺錢。
如果國有企業效益低下只是我國特有的情況,而其他國家卻有很多成功經驗,這表明也許是因為我們缺乏經驗;那么可以堅持資產國有的形式,然后在這個框架內進行改革;可事實是,其他各國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國有企業效益低下是世界性的普遍現象。所以為了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益,各國都普遍實施生產性資產由私人所有,即使有些國家在1950年代被前蘇聯取得的經濟成就所傾倒而將一些企業國有化,結果效益還是很差,于是又轉回私有制;而且后來的事實證明,前蘇聯曾經的繁榮只不過是虛假繁榮,后來眾所周知它自己也搞私有制了。所以現在世界各國都把國有企業的總量控制在一個較低水平。山東社會科學院魯仁研究員承擔的2000年立項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政治性制約因素及梳理對策”表明,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外國的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一般不超過20%,美國不到5%,法國是西歐國家中最高的,為18%。復旦大學華民教授說,1995年世界銀行有一份全球性的調查報告,其基本結論是:國有企業在世界范圍內效益低下,因為它不是盈利的工具,而是政府安定社會、解決就業問題的工具。這是由它產權的公共性所決定的。既然國有企業不是盈利的工具,所以它的數量就不能多,否則一個國家就將沒有能力來負擔國有企業的資金消耗。
為什么從中國到外國,生產性資金由政府經營運作,效益都比較差呢?對此,從外國到中國的大量學者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分析,國內學者在這方面,張維迎是十分突出的一位。張維迎的一些其他觀點我覺得有嚴重問題,這一點我們下面再談,可就這方面的探索和分析而言,張維迎的成就是不容忽視的。他早在1986年就發表了論文,論述了國家所有制下的五個不可能——政企分開的不可能、所有權約束的不可能、解決經營者行為短期化的不可能、預算約束硬化的不可能、經營者與職工制衡關系的不可能。他認為,只要不改革企業國家所有制本身,就不可能解決上述困擾國企的問題。我是在前年讀他的書的,我被他的見解折服,十分贊同他在這方面的真知灼見。
3.國有企業必須改制
面對我國國有企業效益持續低靡的情況,1997年開始,政府開始逐漸放開中小型國企的所有制轉換,而調動國家資源幫助國有大型企業,這也是現在政府采取的政策:保住大型企業的國有性質,保住它們的經營效益;至于中小型國有企業,則可以探索以適當的形式進行所有制轉換。而地方政府則在國有資產所有制轉換上表現出日益高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重大B類項目“改革開放以來非國有企業產權制度與法人治理結構的變遷與創新”的研究成果,對這一現象做了調查分析,該成果說:“隨著市場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存在著先天性體制缺陷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國有企業的經營績效越來越糟,國有企業對地方經濟增長和就業增加以及地方財政的貢獻越來越小,并且日益成為地方財政的包袱。隨著地方政府預算約束的逐步硬化,維持這些無效率國有企業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已經得不償失并逐漸難以為繼。而與此同時,非國有經濟對地方經濟發展和就業增長的貢獻則日益增大,我們的實證模型也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從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出發,對公有制企業進行改制就成為地方政府的最優選擇。”該報告說地方政府的這一舉措是從自身利益出發,這不無道理;可是,它們的這一做法不也對于該省該市的公民有利嗎?如果它們不進行改制,任由自己省市的國有生產性資產越虧越多,不是對大家都不好嗎?就這個意義而言——僅僅在這個意義上——張維迎下面的話是對的:“一個企業的效率只能通過市場競爭來檢驗,如果在原來國有的條件下生存不下了,市場份額不斷縮小,而賣給民營企業,它的市場份額不斷擴大,營業額不斷增長,國家的稅收不斷增加,你怎么能說這種改革不對呢?”“檢驗一個企業所有制的標準,就是在競爭中有沒有競爭能力。我們要相信,我們的改革都是在尋求盡量對大家都有益的結果。”
現在國家重點力保的大型國有企業,大多是盈利的;可是對于它們,學者中還是有人持批評態度,主要是認為它們得到了很多國家行政上的支持,而民企等則沒有得到同等待遇,甚至有些領域不讓民企進入,實行行政性行業壟斷。耶魯大學金融基金學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陳志武在9月30日《贏周刊》上說: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既有國企,也有民企,可是兩者并無可比性,因為國企擁有融資特權、行業壟斷權及方方面面的政府照顧,而民企都沒有。而只要有了行業壟斷權,即使產品差、效率低也沒關系,反正可以多收費。奇怪的是,即使這樣,香港上市的壟斷國企其業績也只比民企高出一丁點,而沒有高出許多。復旦大學的華民教授則說:一些效益好的國有企業,做大并不是靠經營有方,而是靠政府存量,靠權力,靠壟斷,它們的利潤不是財富的增值,而是財富的轉移,是以犧牲老百姓和其他企業的財富獲得的。看看中國幾家大的通訊公司,至今還在向手機消費者雙向收費,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獲取利潤合理嗎?
2004年8月31日《信息時報》報道: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長陳金橋博士日前表示:“資費政策仍然需要考慮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和投資者的利益。”他透露:“電信業在所有中央企業總利潤中,所占份額高達1/3至1/4。所以,站在中央的角度,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是非常重要的。”針對他的這番話,9月3日的《中國青年報》發表盛大林的文章,文章說:
“眾所周知,我國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經濟效益從總體上說很不理想。但就局部而言,中央所屬的近200家國有大企業的效益卻普遍較好。中央大企業上繳的利稅也占了數以萬計國有企業利稅總額的絕大部分。然而,就在這為數不多的中央企業中,電信行業又是鶴立雞群,幾家企業竟然占到了三分之一!這不能不讓人吃驚。電信業為何能獲得如此超額的利潤?顯然是因為壟斷。雖然電信分家后形成了幾家企業,但由于這幾家企業都是一個老板即政府,因此他們之間的競爭非常有限。事實上,電信服務價格至今仍由政府定價,而沒有市場價格。如果電信業是微利甚至賠本經營,消費者當然沒有理由要求進一步降低資費。但現實情況是,電信行業暴利滾滾,憑什么維持如此高的服務價格?‘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當然要考慮,可是‘保值增值’就必然等于‘暴利’嗎?
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石油等行業。最新的公報顯示,中國石油行業的三家國有大企業(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今年上半年就“狂賺”了670億元。其中中石化的利潤同比增長超過50%,中石油也增長了兩成。而這個紀錄是在國際原油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創造的(8月30日《北京晨報》)。中國石油大部分依賴進口,按理說,原材料價格上漲會擠壓下游企業的利潤空間,導致經濟效益下降。近一年來,我國的出租車行業叫苦連天,即為明證。然而,中國石油行業的利潤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大幅增長,這是為什么呢?雖然中國國內的油價也會隨著國際油價的漲落而浮動,但人們看到的情況是:一旦國際原油價格上漲了,中國國內的油價就會馬上跟進;而如果國際油價回落了,中國國內的油價卻往往動作遲緩;而且漲幅總是高于跌幅。
在幾家石油企業先后發出的新聞稿上,都不約而同地用‘創紀錄’這樣的字眼來表達自己的欣喜。石油商們賺了個盆滿缽滿,他們當然高興了。可對下游的消費者以及宏觀經濟來說,這是好事嗎?據有關國際組織統計,每桶石油價格上漲10美元,就會使通貨膨脹上升0.5個百分點,使經濟增長降低0.25個百分點!石油被稱為‘工業的血液’,電信應該可以說是‘社會的血液’吧。石油漲價影響宏觀經濟,電信‘抽血’過多不也影響社會經濟嗎?
其實,作為國有企業,尤其是帶有壟斷性質的國有企業,是不能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的。政府之所以壟斷一些行業,主要的理由是因為它事關國計民生或是國家的經濟命脈。既然‘國計民生’是壟斷的主要理由,那么其經營的依據也應該是‘國計民生’吧!然而,電信、石油等行業的暴利不僅損害了國民的利益,而且也影響了國家的整體利益。盡管這些行業為國家上繳了大量利稅,但這只是眼前的、局部的利益,這樣的暴利是‘與民爭利’的結果,是以損害宏觀經濟為代價的。”
從以上分析我們也許可以得出結論:國有企業的效益是普遍較低的,即使那些國有大型企業有一定的利潤率,很多也是靠行政性壟斷及其他行政支援而來,而且有著其他的社會副作用。正如冀志罡在9月9日《南方周末》上所說,幾個世紀的經濟歷史與經濟理論都證明了,國企的經營績效除非得到政府的特權保護,一般都不如民營企業。而今天街邊的販夫走卒也明白,在公平競爭的條件下,國企的效率遠不如民企。當然,由于大型國企事關國計民生或是國家的經濟命脈,顯然不能進行所有制轉換;按周其仁的觀點,對于它們應該做的是引進市場競爭,破除行業壟斷;我認為他說的很對。可是如果引進市場競爭以后,中國電信或者中國石化出現虧損怎么辦?現在中國四大國有銀行同樣面臨效益低的窘況。10月13日《南方都市報》報道,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作出的一份調研報告表明,目前京城全部37家中外資銀行競爭力排名,四大國有銀行排在最后四名。當然,銀行、電信、石化等行業情況特殊,暫且不說;就目前看,起碼廣大中小國企應該進行所有制轉換;這個過程正在進行之中,其步伐因時因地各有先后快慢不同,但方向應該明確和堅定。
正是在這方面,朗咸平的觀點遭到很多人不同意。朗咸平說,國企的效率本來就比私企好,所以國企根本沒必要改革;他明確地把國企改革中的一切問題歸咎于“新自由主義”,并自稱要用“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來糾正之。我覺得他的這種觀點十分不符合事實。如果因為朗咸平的觀點,造成國企改制的停滯,我認為這是此次大討論所可能產生的最大副作用。當然也有一些人同意他的這一觀點。比如9月18日“新浪財經”報道,經濟學家揚帆說,假設私有企業效率比國企高,有什么有說服力的著作?一定是私有效率高于國企嗎?在不同行業不同時期不一樣,開小飯館一定是私有企業效率高,但是做原子彈、航天火箭誰高?我覺得他的這番話簡直是瞎抬杠,沒有誰說由私企去做原子彈航天火箭;有關國防和國家戰略的建設,當然是由國家來做。又比如有十位學者聯合發表了一份“關于朗咸平教授質疑流行產權理論和侵吞國有資產資產問題的學術聲明”,該聲明說:“‘從資本主義社會走出來的’郎咸平教授抨擊西方產權理論和產權改革誤區,反對把企業、金融和產業等方面存在的一切問題歸咎于公有產權,以為轉制為私有產權便可實現高效率這一流行做法,是及時和正確的。與時俱進的現代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與現代西方產權理論有本質的區別。把國有制和公有制貶為純粹是可用可不用的經濟手段,主張國有制不能與股份制相融合而必須放棄所有股份制企業的國家控股權等,都是不明世界經濟發展趨勢本質的悲觀思維,不利于在推行股份制改革中發展和壯大公有制經濟。我國需要力避前蘇東國家“股大賣小”的特殊私有化道路,因為這條道路不是‘新公有化道路’,而是斯蒂格利茨批評的迷信‘私有產權神話’的邪路。”我覺得這樣的說法并不可取,因為它把討論的問題意識形態化了;這份聲明也表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朗咸平的全面停止國有資產轉換的主張,比較符合一些持左派觀點的學者的看法。
4.國企改制的社會性質分析
讓我們回到開初時談的那1000萬資產的假設。從廣大國民的角度看,假如由政府對這1000萬資產進行決策管理,結果只產出了1010萬、甚至只產出了900萬(虧損),那不是我們所希望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必須改革。我們的第二種選擇是,把這1000萬賣給某個企業家,讓他全權負責經營管理,然后產出1200萬,然后收他的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國家財政得到100萬,剩下的錢就由那位企業家愛干嘛干嘛,我們都沒權去管了。這種做法就是19和20世紀前期西方國家的普遍做法,我們可以將其稱為典型的資本主義做法。這很可能會導致貧富懸殊,會導致巨額財富歸到企業家手中。哈耶克、弗里德曼、諾齊克等人寫過大量著作,論證這種資本主義做法的天然正當性。按照他們的說法,資本家們憑借自己擁有的資產拿走巨額財富是天理應當的,我對此深表懷疑、無法接受,我在剛剛寫完的一本關于政治哲學的書中談了我的分析,有興趣者可以在網上看到。
那么,有沒有第三種選擇,能讓廣大國民充分得到實惠呢?那就是既積極進行國有資產的所有制轉換工作,同時又加強實施累進稅制。我國股息紅利類個稅最高稅率為20%。外國的情況大致是: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分為五檔,最低是15%,最高是33%,澳大利亞最高一檔是47%,德國48.5%,韓國和日本50%,荷蘭53%。我認為,在進行了充分的國有資產轉換以后,可以進一步提高我國個稅中股息紅利類的最高稅率,在這方面拉開檔次,數額較少的股息紅利類收入,可以降低稅率,比如10萬元以下的存款利息稅可以從20%的水平往下調,可是100萬以上存款的利息稅可以從20%往上調。這樣,資產由于由企業家私人經營,也就是民營,效益會比國營提高很多;然后廣大國民從中拿走相當大的一個稅收比例;兩方面結合起來,廣大國民從而因此得到更大實惠,這也就是在一些國家中(比如一些北歐國家)實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或者叫福利社會主義。我覺得我們的改革可以更多參考他們的做法。建國時,我們對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經驗,很多方面照搬前蘇聯的做法,歷史證明這導致了經濟效益低下。但我們也不能搬用美國模式,在美國,資本的勢力太大,兩級分化嚴重。而北歐那些國家既強調市場經濟對于提高效率不可替代的作用,又實施力度很大的國家二次分配以追求平等、促進國民的整體利益,其做法值得借鑒。
這里會出現一個問題。如果對企業家征稅太重的話,他們的投資積極性會受損,他們會賭氣、鬧情緒、消極怠工,從而影響到經濟效益。如果他們的毛利潤是200萬,假設把對他們的總征稅水平從50%提高到60%,那么國家財政就可以由100萬提高到120萬,國家有更多的錢建公園建希望小學。可是,當把稅率做了這樣的提高后,企業家投資決策管理的積極性有可能下降,使得毛利潤從200萬下降到150萬,結果國家財政只能收到90萬。所以,廣大國民必須仔細把握好對資本家階層征稅稅率的度。但不管如何,分配的最高決定權在廣大國民手中,這就叫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一個好的社會,既不能讓官員的權力不受監督約束,也不能讓資本家的利益勢力不受約束監督。這里的關鍵在于廣大人民是否能夠團結得起來,如果各打各的小算盤,形成不了統一意志和合力,那些不法官員和老板就高興了。
前面我們一直在說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轉換,是從“公有”轉化為歸某個或某些特定的個人“私有”,可是如果我們更仔細地分析“私有”這一概念,會發現它其實并不準確。在當代經濟學界和法學界的最新進展中,有很多學者不愿意再簡單地用“公有”“私有”來界定某個資產的所有制屬性。假如張三有1000萬資金,他有權利想拿它投資什么就投資什么,想怎么經營就怎么經營,投資所得全歸自己所有,所有這一切都得到法律的承認和保護,那確實可以說:這一千萬是張三的“私有財產”。可是,如果法律并沒有賦予張三對于這1000萬這么大的權力,而是規定了一系列限制,比如不能進行壟斷性經營,不能生產有損消費者健康的藥品,不能作太過性感的廣告;特別是從這筆資金獲得的收入并不都歸張三所有,張三甚至都不能自己決定自己到底能從那200萬毛利潤中得到多大的比例,因為廣大國民既可以把總稅率定為50%,也可以定為60%,甚至更高,只要符合民主程序,就是合法的。這時我們就不能簡單地說那1000萬是張三“私有”的。很多外國的政治思想家(比如羅爾斯)都支持這樣的法律規定,而資本主義的倡導者對此是十分反對的,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的第二編“超越最弱意義的國家”第二節中,就指責羅爾斯主張的分配方式是社會主義的;他認為如果按照羅爾斯的思想,那么資本家擁有的資產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變成公有的了,因為全社會都對那1000萬資產的使用和收益有發言權。在諾齊克、哈耶克這種資本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心中,社會主義、資產公有是天然不對的;可是在我看來,社會主義、資產公有恰恰是天然正當的。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那1000萬張三的“私有財產”:全體13億中國人一致同意,把這1000萬委托給張三打理,如果張三經營管理有方,人民不會虧待他,他能得到不菲的一筆報酬;可是究竟這筆報酬是多少,是人民而不是張三來定。而且張三在經營時,必須遵守人民作出的種種法律規定。張三去世后,這筆財產及其收益的累積,必須以遺產稅的形式交一大筆給回國家財政。而如果發生了戰爭、嚴重的饑荒等緊急情況,13億人民認為有必要征用張三那1000萬資產,那么就有權征用,張三如果抗辯說這筆財產是我的你們無權征用,這種抗辯在道德上是無效的。休謨在《對道德原則的探詢》187頁對這種征用的理據何在作過很好的分析。因此,說那1000萬資產就是張三“私有”的,顯然片面;更準確地說應該是:那1000萬在相對的、一定的意義上是張三“私有的”,可是在絕對的、完全的意義上,是全體13億中國人民“公有的”。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說,今天我們進行的所有制改革,與其說是從“公有”轉換為“私有”,不如說是從一種社會組織形式的“公有”轉換為另一種社會組織形式的“公有”,一種效率更高的“公有”。
以上我們談的是要不要進行國有資產的轉換,如果大家能夠達成共識:目前起碼對廣大中小型國企應該進行轉換,那么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轉換?
二、如何進行國有生產性資產的所有制轉換
某個省有一個中型國有企業,現在有10座廠房、100臺機床以及其他設施,還有120萬資金以及320萬欠債,等等。因為經營效益比較差,一直虧損,所以從當地政府到其員工,都認為應該對它進行所有制轉換;那么,怎么進行?
第一種選擇可以叫做“證券平分式”模式。
這種做法是,完全按照“省屬國有資產”的定義,把這筆資產平分給該省全體3000萬人民。可我們不可能把那廠房、機床、扳手、油漆等平分給3000萬人民,我們必須把這些轉換成貨幣形式,才可以在3000萬人中平分。怎么轉化成貨幣形式?就是采取十二年前的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采取過的“證券方法”,金雁《新餓鄉紀程》的142至143頁對此有具體說明。先由國家將準備私有化的國有資產進行估價,比如假設對上述那個中型企業估價為1200萬,然后就印發面值為1200萬的“資產證券”,把這1200萬的資產證券無償平分給全省3000萬人。就公正的角度看,這也確實可以說是公平的。不管你原來是在效益好的廠還是效益差的廠,不管你以前對國有資產貢獻得多還是少,這些差別細算起來是算不清的;而且在效益好的廠、或者對廠子貢獻得多,很可能原來就拿了較多工資獎金。總之,現在就徹底平分了,每個人都拿到了比如說面值二萬盧布的十張“紙”。
可是,什么叫作“面值二萬盧布”?我們知道,貨幣的價值是在正常有序的市場經濟運作中確定的,一元盧布能買一只老母雞還是只能買一個雞蛋,不可能人為地統一規定,一元盧布的價值只能在正常有序的市場經濟的生產和交換中才能得到有效確定。像前蘇聯那樣由國家對龐大的國有資產存量進行統一估價,估出來的價格很可能嚴重偏離其真實的市場價值,巨額數量的這樣的“證券紙”進入市場,對正常的市場經濟運作造成了嚴重擾亂。而且把證券化以后的資產平分掉的做法,也給原本有序的分工合作的工商業生產交換體系帶來很大混亂;無償分配使股權過于分散,形不成對企業有責任能力的控股階層,從而在一定時期內使已“私有化”的企業處于“無主”狀態,不能實現股份制企業的規范運作。結果這一切就造成國民經濟迅速下滑,后來那些“紙”在市場上根本買不到什么商品,1992年初230盧布能兌換到1美元,半年后就必須600盧布才能兌換到1美元,當時的俄羅斯老百姓紛紛廉價拋售手中的“證券紙”,結果造成后來出現一些金融寡頭、資產巨鱷。所以說,“證券平分”的做法固然公平,但是嚴重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進行,對經濟建設造成了很大傷害,這使得當時的蘇聯東歐百姓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所以,我們今天不能使用這種方式。百姓出于公平感做出或者支持的一些行為,有時的確會反過來傷害百姓自身。出于公平感當然是對的,但是滿足公平感的方式途徑往往不止一種,我們應該運用社會理性,找到既能滿足公平感、又能滿足其他社會效應(比如效率)的方式途徑。
第二種選擇可以稱作“拍賣競投平分式”模式。
不是發“證券紙”,而是通過市場拍賣競投,把上述那個中型企業轉換成現金,比如說1000萬,然后平分給全省3000萬人。拍賣競投是把這個中型企業的現有物質存量轉換為現金的公正做法,符合“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打個比方,假設這個企業完全是某個個人比如張三的,他現在想出售這個企業,為了把那10座廠房100臺機床1000個扳手10000桶油漆盡可能賣個好價錢,他會不斷地和各個可能的買家見面,千方百計地和他們討價還價,他不一定要用拍賣競投的方式,一樣可以實現自己的最大利益。可是我們說那個中型企業不是某一個人的,而是全省3000萬人的,不可能3000萬人整天什么事不干,天天一起去找各個可能的買家討價還價;只能請一個或幾個人去操辦這件事。可是這就立刻出現“人困境”:如果全權交給李四去辦,我們這3000萬人如何能相信李四就不會和買家串通一氣?本來那些廠房機床扳手油漆可以賣1100萬,有人想出這個價;可是李四偏偏要賣給另一個人,比如搞“管理層收購”(MBO),因為雖然這個人只出800萬,但他愿意給李四200萬回扣。可是那3000萬人怎么知道到底有沒有人愿意出1100萬?他們不可能天天陪著李四、和他形影不離。為了防止李四貓膩,3000萬人就設計出拍賣競投的方式。這樣,雖然3000萬人不能天天和李四在一起,但在那一個拍賣競投的時刻,通過各個媒體,大家可以把目光聚焦在拍賣競投的大廳里,所有可能的買家都會出現在那個大廳里;這樣,李四玩貓膩的可能性就被基本杜絕了。所以現在城市土地也都采取拍賣競價的方式出售給房地產商,而政府用品的采購也越來越多地采取招標競價的方式。因為公共財產的出售或者購買,一定有一個全體國民對政府這個公共管理人的信任問題,而拍賣競投這個制度設計能很好地解決這個信任問題。
這其實是個簡單的道理,而對于從這個問題引發出來的種種經濟、政治現象,秦暉有詳細、精辟的分析,有興趣者可以看他最近關于“朗顧之爭”發表的文章。我對秦暉十分敬重,這不僅是因為他深厚的學養和精深的見解,更因為他始終堅持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吁求社會公正。其實張維迎也一定明白“如何信任人”的道理,他寫過一本書《信息、信任和法律》,就是專門探討社會運作中法律、責任和信譽、信任的關系。可8月24日在接受《經濟觀察報》和《證券市場周刊》采訪時,每到涉及如何公正轉換國有資產時,他總是避開,而是大談轉制后效益如何比以前高、轉制如何是一個創造財富的過程、一些民企老板買了國企后如何反而虧了、更嚴重的問題是國家政府部門對私人資產的侵吞,等等,就是不談必須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公正轉換國有資產。當記者問到他如何看待MBO方式時,他說了一大堆話來為MBO辯解。他真的不明白:直接把企業賣給企業管理層,中間很可能發生貪官和企業管理層串通謀利?他的一個中心意思就是:趕緊轉制,轉了制后企業效益才能提高;至于怎么轉制,大家不必在這方面太在意。可是,大家能不在如何轉制上在意嗎?那可是直接關系到千萬國企職工安身立命的大事,是關系到公共財產是否能保值增值的大事;現在很多人在這方面指責張維迎,我覺得那都是他應得的,我覺得他的立場確實坐偏了。8月28日在“中國企業家經濟高峰論壇”上,他居然說出這樣的話:“是自己生一個孩子,還是收養一個孩子?我的建議是,從個人角度,應該自己生一個,長大了不會發生感情糾葛問題,但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收養一個孤兒可以為社會減輕一些困難。同樣,如果以個人利益來說,我勸民營企業家還是離國有企業越遠越好,否則最后你可能被說成侵吞國有資產。但是為了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還是應該救救國有企業。”明明是一些民企老板想在缺乏民意監督的情況下,和某些貪官達成交易,以盡可能低的價格收購國企,這是一種不合法的自利行為,但張維迎卻要把它說成是這些老板為國為民慈善的義舉,我看了這話簡直要吐,向老板獻媚也不是這種獻媚法。現在眾多市民通過網絡對朗咸平表示支持,朗咸平的功績正在于把轉制中的公正問題大張旗鼓地提了出來,正是因為他的大聲呼吁,轉制中的公正問題現在成為上上下下關心的問題。盡管在我看來,朗咸平的論述確有很多自相矛盾、思維混亂之處,有很多觀點我也不能同意,但他能如此強烈地把“轉制中的公正”這個問題提出來,單憑這一點,就已經對中國社會的進步立下大功。
我們接著談第二種選擇。當通過拍賣競投將上述那個中型企業的資產存量完全轉換為現金,然后還清欠債,得到比如說1000萬,需要首先對原職工做解聘時的補償安置,可能要拿出500萬,然后把剩下的500萬在全省3000萬人中間進行平分。我贊同拍賣競投和補償安置原職工,但不贊同把剩下的500萬平分掉。因為那樣一來固然是真正“藏富于民”了,可是我們共同的社會生活需要大量社會福利性和公共產品性資金,這些資金必須聚合才能有效地為每個人提供福利保障和公共產品;尤其在當今社會急劇轉型的時期,為所有人提供生活保障十分重要。把錢先分掉然后再設法聚合起來,我覺得沒有必要。
第三種選擇可以叫做“拍賣競投全民福利保障式”模式。
當我們看清楚前面兩種選擇的利弊之后,很自然就得出了這第三種選擇。這其實是很多有識之士很早就提出的觀點,我在這里把他們的觀點做一個概要。那就是,通過拍賣競投向國內外的投資者出售中小型國有資產并還清欠債,所得先用來補償原企業職工;周其仁以大量的實證研究說明,這時必須充分考慮對中老年職工的補償,他們多年為企業工作,拿的工資比民企外企職工的工資都低,現在企業破產了,必須對他們作一個充分的補償。如果這個企業賣到了1000萬,可能不能只拿出500萬補償職工,而要拿出600萬、700萬。剩下的錢全部進入國家財政,大部分做失業、退休、醫療等社會福利保障基金,政府不要再拿這些錢去投資辦廠了。這會使短期內國家財政收入增加很多,而由政府支配的財富如果在國民總財富中比重太大,對于社會經濟的整體運轉也有弊處,所以可以考慮在這段時間內,比如三年五年,按同一比例對全民統一減稅。總之,在體制轉型中,我們既要完成轉型任務,使得新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十分有效率;又要在轉型過程中堅持社會公正,并千方百計地減少民眾的陣痛、減少社會的振蕩,使社會經濟的運轉始終保持一個正常有序的態勢,避免轉型期可能出現的混亂。
以上我們談了三種選擇,結論是第三種選擇應該是我們真正的選擇。
我們為什么要堅決反對“管理層收購”(MBO)的做法?因為這種做法不符合“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它給貪官與原管理層達成某種幕后交易、賤賣國有資產,預留了很大的空間。的確,在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中、在各種形式的轉制過程中,存在著很多竊取國有資產的情況,但那畢竟是非法的,所以貪官和奸商會有所畏懼;可是當MBO變成一種合法的做法時,貪官奸商對法律懲處的畏懼大為減輕,因而通過MBO方式串謀竊取國有資產的做法就可以加大力度。9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國資委的文章,對MBO叫停,這可以被看作此次大討論的直接成果,這就是“公正”的勝利。
這次朗咸平指責了三家公司海爾、TCL和格林柯爾,它們和本文的觀點是什么關系?對于朗咸平的指責,周其仁在《經濟觀察報》上有一篇訪談,題目是“周其仁:我為什么要回應朗咸平”,談了關于這三家公司的看法。關于這三家具體的真實情況到底如何,我并不清楚,所以我不能對這三家公司的行為作出評論。但我們可以就周其仁的話進行一些討論。在我們全部上述分析中,談的是這樣的企業:企業是由國家的資金投入建立的,比如1000萬,后來總是效益很差乃至虧損,于是現在要競價出售。我們把這種情況統一給一個概念“國企改制”。可是,有一些情況是不屬于這個概念之內的。
第一種,如果一個企業在20年前建立,100個人每個人投入1萬元,有一個極有能力的企業家和一個強有力的管理團隊,這在法律上被稱作集體企業;該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得了驚人的成就,20年后的今天企業資產600億。現在該企業在進行產權方面的改革理順工作。這和本文主旨沒什么關系,它根本就不是國企,而是集體所有制企業。所以在該企業里也沒有什么國有資產流失方面的問題。按周其仁的介紹,海爾就屬于這種情況。第二種,如果一個企業10年前完全由地方政府投資1000萬建立,也有一個極有能力的企業家和一個強有力的技術管理團隊,先規定好:如果企業盈利,該企業家及技術管理團隊的人能拿多少報酬;還規定,從這些報酬中必須拿出特定比例購買本企業股權,以在這些高管和該企業間建立起牢固的長遠利益紐帶。10后的今天,企業資產30億,為15億股,該企業家持有其中1.5億股。該企業現在仍然效益很好,仍在迅速發展。這種情況同樣和本文主旨無關。按周其仁的介紹,TCL就屬于這種情況。至于格林柯爾轉制情況,周介紹說:“科龍公司所在地鎮政府的頭頭憑控股權到科龍當了家,格林柯爾是從這個頭頭手里收購科龍的。”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因為這最關鍵的一句話含義不明,我們只好不予置評。好在這和本文主題也無多少關系。
有一點需要明確,像TCL這種效益非常好的國企,在整個國企中占多大比例?如果占到很大比例,那么本文的觀點就全部站不住腳。當然我看到的所有事實材料都告訴我:像TCL這樣既沒有得到行政壟斷的支持、效益又這么好的國企,在全部國企中占的比例非常小,所以我才會寫這篇文章。反過來說,朗咸平是在整體上論述國企改革的,他就必須在統計學意義上描述所有國企(比如說100萬家)的整體風貌,他找的例子也應該是體現這一統計學意義的典型樣本。打個比方,他要給我們描述今天臺灣青年的總體戀愛狀況,為此找了三對戀人做例子,結果他找了一對香港人、一對臺灣同性戀者、還有一對不知所云。為什么要找這三對完全不能代表臺灣青年總體戀愛狀況的戀人做例子?就因為這三對戀人都是明星?能吸引眼球?所以說朗咸平經常自相矛盾、思維混亂。他還自稱財務方面是“亞洲第一”,有這種思維混亂的“亞洲第一”嗎?如果談動機的話,朗咸平對公平的大聲疾呼,更多地是出于嘩眾取寵、博取眼球;他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采訪時,十分可愛地、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出名后的喜悅之情:“我現在真是在內地大大地出名了。”他之所以會提出一些荒謬的、自相矛盾的觀點,正是因為這些觀點能夠聳人聽聞;至于這些觀點對不對、有多少理據、相互間是否連貫一致,那是次要的,關鍵是要一鳴驚人,讓自己的大名在短時間內家喻戶曉。當然,歷史的奇妙就在于,對歷史進步立下功勞的行為,經常是動機談不上高尚的。
三、結語
今天我們進行的國有資產改革必須同時滿足兩個要求:效率和公正。為了效率,我們要把中小型國企出售給私人,然后把出售所得放進國庫作全民的福利基金,這實際上是從一種形式的“公有”轉化為另一種形式的、效率更高的“公有”;雖然進行轉制,但宗旨沒變:為了更好地滿足全體中國百姓的利益。為了公正,我們在出售時必須采取“公開、公平、公正”的拍賣競投的方式。
我們不能因為要效率,所以就通過什么方式出售都可以;張維迎就是這樣勸大家:關鍵是要創造財富,至于如何轉制、如何分配,那是次要的,不必太在意;我們不能聽他的勸。我們也不能因為要公正,就采取“分掉”的方式,更不能借口說“公正”的方式現在因為種種限制實行不了,所以干脆不進行轉制了。現在我們完全能夠進行拍賣競價,完全能夠按照“三公原則”出售中小型國企。朗咸平就是這樣勸大家:關鍵是要公正,如果轉制中出現很多不公正現象,我們就應停止轉制。我們不能聽他的勸。
因此,對于中小型國企轉制方面的每一個舉措,我們都必須同時從兩個方面去判斷它是否正確。其一,它有沒有積極推行轉制。如果它保守、拖延,即使不像有的學者說的會使國有資產爛掉,也很可能會使國有資產在損耗、在減值;那就是對國有資產不負責任,就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今年轉制,能收回1000萬;明年轉制如果只能收回900萬,那不是流失了100萬嗎?其二,它有沒有“公開、公平、公正”地進行轉制,有沒有采用拍賣競投的方式?(不排除有其他的符合“三公原則”的公正的轉制方法)如果它沒有做到這一點,也是對國有資產不負責任,也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假如通過拍賣競投能收回1000萬,結果用MBO只收回900萬,那不是流失了100萬嗎?這兩個標準必須同時使用,只要有一個標準沒達到,這一舉措就是不正確的。
當朗咸平和張維迎進行爭論時,雖然交鋒激烈,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效率和公正只能要一個。朗咸平說因為國企改制中存在種種不公正,所以干脆國企改制叫停;然后他閉上眼睛進一步說:國企效率比民企好。張維迎說只有改制才有效率,“離開社會總財富的增加,糾纏于分配問題,是沒有意義的。”不僅是他倆,我想很多人都有這種效率公正不可同時兼得的觀點;就像一位男子同時遇上西施和貂蟬,因為婚姻法一夫一妻的規定只能痛苦地娶走其中一位。在對社會價值目標的追求上,決沒有這種限制,只要大家都有足夠的社會理性,我們完全可以、完全能夠同時實現效率和公正。
張維迎說,要善待民營企業家這些對社會作出貢獻的人;我很同意他這句話,我想進一步說,我們應該善待每一個人。確實有一些民營企業家做出了一些和貪官串通、低價購買國有資產的行為,這是必須予以譴責和懲處的;可是我們不能因此就忘了他們對社會作出經濟貢獻的一面,在我看來,企業家是目前中國最需要又最緊缺的人才。同樣道理,那些貪官也必須而且理當受到譴責懲處,可是他們也為社會在公共管理上作出了很大貢獻。現在一些學者在探討企業家和官員的“原罪”問題,我更愿意同意孟子的“性善論”。每個人都是有“善根”的,可是沒有社會性監督制約,每個人都會辦壞事、說壞話;而有了社會性監督制約,每個人都會辦好事、說好話。一些人之所以辦了一些壞事、說了一些壞話,只是因為以前沒有遇到社會性監督制約,沒有在辦壞事說壞話的萌芽狀態就受到抑止。因此,這次朗咸平引發的大討論實際上是在對企業家、官員、學者進行社會性監督制約,用廣泛的人民意志督促、鼓勵每一個企業家、官員、學者辦好事、說好話,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全部用來為百姓作貢獻;只要這樣,老百姓決不會虧待他們。說到底,我們都是祖國大家庭中的一員,如果每個人都能按公理說話辦事,大家團結合作、互助友愛、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不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