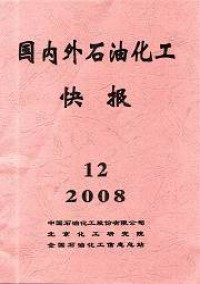國內傳統中庸之道的討論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國內傳統中庸之道的討論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傳承民族文化,對今天的文化建設十分重要。但是,在我們進行民族文化傳承的時候,我們也不要忘了一句經典的話:批判繼承!我們要傳承的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在國學啟蒙的時候,我們要提倡“站著讀經典”。
最近,再讀的始末,參觀了劉光第先生的墓,有很多感慨,我將陸續貼出有關博文。
現轉摘博友月邊漁與花如箋的博文《淺論中庸之道》于下,對當前的國學啟蒙或許有些啟發。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倫理學和方法論。孔子在《倫語雍也》中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意即中庸是一種最高的德性,人們很久都不具備這種道德了。“中庸”也叫“中道”,“中行”,意為“無事”與“不及”,即對立的兩端之間的調和與折衷。《中庸》指出:“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這種所謂的“執兩用中”之說,亦即中庸之道。北宋的程頤解釋道:“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后來又解釋為:“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
對“中庸之道”,不少人以為是修身養性的根本,甚至某些所謂的權威們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中庸之道”的種種好處。依筆者看,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社會的存在,中庸之道功莫大焉;中華民族兩千多年徘徊不前的事實,中庸之道禍莫甚焉。要想發展,要想進步,要想使中華民族永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堅決、徹底、干凈地肅清仍流布于中華大地上的中庸之道思想。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庸之道是阻礙中華民族進步的禍根。
一、中庸之道培養了大批鄉愿之徒
鄉愿是什么?鄉愿就是和事佬,就是和稀泥,就是“不騎馬,不騎牛,騎著毛驢走中游”的所謂的中間路線,就是毫無個人觀點,唯主子之意旨行事的奴才思想。表現在政治上就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保命哲學,是一種道德極其敗壞的行為。
中國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在《孟子·盡心下》中對鄉愿有過這樣一段鞭辟入里的描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又說:“閹然媚于世也者,鄉愿也”。意即那種八面玲瓏,四方討好的便是鄉愿。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在一首《千年調》的詞中這樣描繪鄉愿:“然然可可,萬事稱好。”“寒與熱,總隨人,甘國老。”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先驅章炳麟(太炎)先生在1906年撰寫的《諸子學略說》中直指“中庸之道”的實質是叫人做“鄉愿”,即當兩面派的偽君子。
對于深諳“中庸之道”實質的鄉愿來說,自以為得了孔孟的精髓,無論做什么,都隨大流,絕不當出頭鳥,絕不做出頭椽子,哪怕火燒眉毛,哪怕國難當頭,民族危亡,就是看得再清楚,也絕不先于人言,先于人去做利國利民的些微事情。這種人純粹是墻頭上的草,東風西之,西風東之,毫無個性,毫無主見。可就是這批毫無骨氣,毫無人格可言的鄉愿,卻偏偏在“中庸之道”盛行的中國吃得開,行得通,顯得很有人緣。而且因為他們的影響,中國人中的絕大部分都具有這種唯唯諾諾,不敢為天下先的鄉愿思想。若林則徐等“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的大仁大德之輩,他們是百般詬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二、中庸之道讓一批昏君肆意虐民
因為孔子在《論語泰伯》中說過“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的話。所以,這幫得了中庸精髓的人,便在昏君不理朝政,大肆虐民時,學會了一套“忍”的方法。什么萬事忍為高,什么忍字頭上一把刀,什么能忍則忍。什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明君盡忠可以,對昏君暴君也可以盡忠嗎?乃至清末權臣李鴻章也撰寫了一幅“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心中一段春”的對聯,來表明自己的忍。談到這里,筆者不得不說,孟老夫子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浩然正氣,才是中國人應該也必須具備的。他的“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股肱;君視臣如股肱,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糞土”的錚錚鐵骨,令筆者佩服得五體投地。可惜,孟老夫子的影響遠不及孔子。
歷朝歷代的君王中,禍國殃民的昏君舉不勝舉。如此昏庸無道的君主為何沒人去推翻呢?為何讓他們如此肆無忌憚地禍亂國家呢?因為孔子認為昏君、暴君不該誅,殺了就是犯上作亂。昏君、暴君可以肆意危害百性,百性不可以有一點的想法去危害暴君。如孔子認為春秋時代是“禮壞樂崩”,“臣殺君,子殺父”,“邪說暴行”不斷發生的糟得很的大亂局面。可是同時代的師曠則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欲?”(《左傳襄公十四年》)意即天是非常愛護百姓的,豈能容忍暴君荒淫,作威作福?被驅逐出國是罪有應得。公元前510年,魯昭公被三桓(季孫、叔孫、孟孫三家)趕出國外后死亡,晉國的史墨評論道:“魯君世縱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憐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左傳昭公卅二年》)就是說,魯君一代代放縱,這樣的國君流亡死去,誰會憐憫?國君的位置本來就不是固定的。倘若歷史不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是采用師曠、史墨這些富有民主思想的先驅的理論,或者奉行孟子“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思想的話,工業革命未必不首先在中國發生。自鴉片戰爭以來,屢受列強侵略,蹂躪的歷史未必不會改寫。可惜,一心為了劉家江山的漢武帝聽從了董仲舒的愚民建議,并把它作為國策固定下來,并為以后各朝代所效仿,嚴重束縛了人民的正常思維,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從這點上,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孔子、董仲舒等一批主張愚民政策的人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三、中庸之道為統治者培養了大批順民,也讓一批奸佞之賊穩居高位
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歷朝歷代都出現大量穩居高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奸佞之賊,如唐玄宗時的的李林甫、楊國忠;宋徽宗時的蔡京、王黼、朱勔、李彥、童貫、梁師成等“六賊”;明朝的嚴蒿、魏忠賢;清朝的和坤等。他們之所以能呼風喚雨,肆意殘害忠良,一是得了昏君的寵愛,二是在中庸思想的影響下,沒有敢于揭發他們罪惡的忠貞之士。雖然士大夫看得都很清楚,知道他們在禍國殃民,可是誰也不愿當這個出頭的椽子,而是聽任他們胡作非為。至于百姓,因為孔子有“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的話,所以更不敢出頭,而是安于當順民。
最典型的當數南宋高宗趙構時的奸相秦檜。昏君趙構為了自己的帝位,不惜置江北大好河山于不顧,只圖偏安于江南一隅。秦檜則秉承趙構的意者,以“莫須有”的罪名害死了抗金英雄岳飛。聽到岳飛被害的消息,“天下聞者,無不垂淚,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檜。”
為什么都埋怨秦檜而不去埋怨那個老混蛋趙構呢?還是因為孔子的正名思想,孔子的中庸之道。那個老混蛋是正統,是他媽的真龍天子,埋怨他就是大逆不道,就是犯上作亂,就該株連九族。那為什么只埋怨而不去揭發秦檜的罪行,以使全國人民共憤呢?又是那個中庸之道作怪,秦檜是皇帝跟前的紅人,操著生殺大權,誰會去冒這個大不韙呢?不能當出頭鳥,保住富貴,保住性命才是第一位的。終于在趙構和秦檜死去若干年后,因為后繼皇帝政治和軍事上的需要,才對岳飛平反昭雪,也才有了民眾阿Q式的精神勝利。
由此,我想到了從有關資料上看到的一件真實的事情,抗日戰爭初期,一個班的日本鬼子擄掠了200多強壯的中國北方男人,而后不用捆綁的押解著他們準備去處決。因為天熱,這一個班的日本鬼子又走了一多半去找水,只剩下三四個鬼子看著。我們愚鈍到極點的同胞竟沒有一個想領頭反抗,逃跑的,而是聽任其他的鬼子回來后,把他們押解到一個坑里活埋了。這是說的老百姓。同樣是抗日戰爭初期,近百個日本兵,押解著五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去燕子磯槍殺,可憐這五萬名軍人,不要說反抗,連逃跑的勇氣也沒有。我們在責罵日本鬼子毫無人性的同時,難道不對我們同胞的行為反思一下嗎?他們為什么沒有反抗精神?為什么安于當順民而任人宰割?抗日戰爭,如果沒有輩的昂起頭顱,挺直腰桿,以大無畏,不怕死的剛烈血性與日本鬼子拼殺,則未必只有八年。
四、中庸之道使人們不敢有創新意識,只能步人后塵甚至固步自守。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民族不竭的動力。一個沒有創新意識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
中華民族本來是一個最有創新意識的民族,在中庸之道的流毒傳播不廣時,中華民族的創新和進取精神是最強的。他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創造了輝煌,成為領先當時世界潮流的優秀民族。比如商鞅變法、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王安石變法、乃至后來的康乾盛世等,都是因為受中庸之道的影響小才得以發展起來的。
凡是中庸之道影響廣、中毒深的時代和地區,其發展速度都是異常緩慢,甚至停滯不前。
再如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南方和沿海地區為什么比北方和內陸地區發展快呢?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地方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中庸之道思想對他們影響甚微。
孔子對統治者大加吹捧,時時處處替統治者著想,建立了一整套為鞏固統治者的統治地位含有嚴重愚民政策的理論。就是這套理論,被歷代統治者奉為圭臬,成為愚弄人民的工具,成為茍延封建統治的利器,成為束縛人們正常思維的羈絆,成為阻礙中華民族進步的禍根。
以上僅是本人的一管之見,而且言論未免偏激,懇請有識之士匡正。謝謝!